2022年10月下刊
「唔怪之得」;your smell attracts mosquitos;Jingyao 案梳理;校園性暴力;洗碗呢件事;人類體温;戲劇性氣候抗議;《金髮夢露》;Mobile Gambling;台灣經濟;青年選里長;Little Rituals;美國中期選舉催票議題;「中國式家長」;Why Socrates Hated Democracy;普通人喺極權社會;Iran Protests;四通橋抗爭;離開與留低;「外婆」vs「姥姥」;蔡雲峰;《小熊維尼》真實世界;Best-seller novelist;輿情「王牌小編」;外交官分析俄羅斯;
- 「唔怪之得」

好慚愧,呢個粵語 blog 好少分享粵文 or 粵語知識。今次係因為同一班 fri 傾偈引出嚟嘅話題,所以揾到呢篇文章考究一啲用法嘅演變,都幾得意,嫌麻煩嘅話可以直接睇結論:
按照推論,出現次序依次應該係「唔怪得」>「唔怪之得」>「怪之得」>「唔怪得之」>「怪唔得」「怪唔之得」「怪唔得之」。
即係四個入面,「唔怪之得」應該係最早出現嘅。
至於用邊個好,大家鍾意就得。
- your smell attracts mosquitos
Washington Post|Are you a mosquito magnet? It’s because of how you smell.
打破迷思,同血好唔好飲真係完全冇關係㗎
當然,如果你本身就好易惹蚊,就要記得着長衫長褲,搽\噴驅蟲水喇,特別小心傍晚前後兩個鐘係乸蚊嘅活躍時間;同埋可以多啲沖涼去沖走皮膚上嘅物質
Just by breathing, we’re broadcasting to mosquitoes that we’re there, said Leslie Vosshall, the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at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and the lead researcher behind the new study.
The study found that people like subject 33, who have higher levels of compounds called carboxylic acids on their skin, are more likely to be “mosquito magnets,” Vosshall said.
All humans produce carboxylic acid through sebum, a waxy coating, on their skin. The sebum is then eaten by the millions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that colonize our skin to produce more carboxylic acid. In copious amounts, the acid can produce an odor that smells like cheese or smelly feet, Vosshall said. That smell appears to attract the female mosquitoes on the hunt for human blood.
“If you’re a mosquito magnet today,” Vosshall said, “you will be a mosquito magnet three years from now.”
The study didn’t ans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more carboxylic acids on their skin than others. But, Vosshall sai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kin microbiome is unique in every individual.
“Everybody has a completely unique village of bacteria living on their skin,” Vosshall said. “Some of the mosquito magnetism differences we’re seeing here may simply be the differences in types of bacteria.”
- Jingyao 案梳理
一份好好嘅梳理,呢四年,噉樣回顧返,都有唔少嘅進步,難肯定仲係好難,但起碼我哋可以一齊將佢變得更容易啲
still long way to go. Just believe
- 校園性暴力

震驚之餘,人們也對黃姓教師發出嚴厲的譴責,紛紛以「狼師」、「人渣」稱之,顯示了人們對於此類犯行的深刻厭惡。同時,利用這樣的語言,我們也得以在自己與「惡行」之間拉開距離,將性暴力視為一種非人的「例外狀態」——只要制裁或「消滅」了邪惡的行為人,性暴力就會消失。
然而,性暴力只是「一人之惡」嗎?事實上,正如蔡宜文在評論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時所言:「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這句話的意思並非行為人本身沒有責任,而是說明了性暴力的「社會性」:性暴力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它被我們日復一日所習慣、仰賴並鞏固的體制忽視、縱容,甚至餵養、鼓勵。
這個體制指的是,父權社會的性別文化將女性定義成性的付出者,男性則理所當然地獲取來自女性的性服務,甚至成為掠奪者。而在這起校園性誘騙事件裡,我們還可以更具體地討論多個共同交織運作的結構,包括:升學體制內的校園文化及師生權力不平等;父權性別文化下對女孩的情感教育;年輕女性如何在被要求執行特定情感義務時,自身的情慾卻又受到貶低;以及男性對女性的性征服如何被視為陽剛氣質和「阿爾法男」(alpha male)身分的證明,年輕女性又如何因為各種性別規範,而特別容易成為被獵捕之對象。
我們必須深刻的認知到,父權社會裡的各種性別規範如何結合其他的壓迫體系,進而縱容甚至合理化性暴力的發生。
這一方面包括了檢討父權社會所假定的男性資格感和特權;我們必須挑戰男性作為情感和性勞動的獲取者的地位,並且不再把男性在性方面的進犯和掠奪視為一種正面的陽剛表現,進而給予獎勵。進一步來說,我們應該反省父權社會的陽剛崇拜,拒絕那些有毒的陽剛氣質。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賦予女性更多的資格感,尤其這樣的工作必須從小就開始進行。我們要鼓勵年輕女性表達負面的情緒,並懂得拒絕,不再假設女性必須表現出溫柔、傾聽等傳統的陰性特質;我們要教導年輕女性用多樣的方式處理衝突和爭端,以及敢於說出不同的意見,不需要害怕自己會因為「直言」而不符合女性氣質。我們更要支持女性為自身爭取權益,而不是要求他們總是以他人的感受和舒適為優先考量。
最重要的或許是,我們必須教導與鼓勵年輕女性認識、探索自己的身體和情慾,不僅僅是懂得拒絕自己不想要的觸碰與互動,而是更積極地,讓年輕女性得以練習表達自己的「所想」和「所欲」,得以認識到什麼是讓自己愉悅的正向性互動,並且鼓勵她們可以主動地追求這些慾望和互動。
因為,唯有當女性得以認識、了解並自由體驗帶給自身快樂與滿足的情感和慾望交換時,她們才能夠更積極的辨識、拒絕、甚至抵抗那些自己所不想要、不喜歡、不認可的侵犯和傷害。
- 洗碗呢件事

我成長的家教其實算不上非常嚴苛,但除了撒謊等原則性問題,父母還有一些對我頻繁嘮叨的要求,例如不要隨手放東西、房間不能太凌亂、聚餐時要幫忙收拾等。只是我後來才意識到,一些禮數的規訓是有性別的,我和我的妹妹們往往會被期待安靜、整潔、懂得照料家務事,但他們從不要求我的表哥堂弟去洗碗,就好像他們不會做,好像雜亂玩樂是男孩的天性,而女孩要「生來愛乾淨」,生來就會做這些收整、打理等細緻的事。
我家裏父母是輪替洗碗的,甚至因為媽媽不時要加班,所以爸爸洗碗更多。即使如此,我爸還是時常會被媽媽嫌棄洗碗沒有擦拭灶台和洗碗池,無意間,我也形成了每個細節都要井井有條的印象。但我家裏男性照料家務更多的樣子,若轉向和外部交流的聚餐場合,角色也會立刻調轉。
看似是有點刻薄,但在追問為何做飯有男有女、洗碗多是女性時,我忽然意識到,普遍的家庭分工和社會分工是如此相似,如同秘書、清潔工多性別為女一樣,家庭裏,女性也往往承擔著最瑣碎、細節的勞動。料理往往帶有廚師的個人特質,做飯的人可以享受人們對食物讚美的價值反饋,但洗碗是簡單、重複、沒有創造力的,洗碗的人常常在飯後交談不被看見的盲區。
以前總不理解為何媽媽每次聚餐洗碗的時候都要叫我去聊天,現在會對每個在我洗碗時默默站在門口陪伴的朋友多一分喜愛。
有一次女友在我家住了兩天,爸媽不在,但姐姐和姐夫們也過來了,對我們來說,那個場合有點臨時和隨意,因為家長不在。晚餐叫外賣,但用了一些碗筷,吃完飯,我突然意識到出現某種奇怪的氛圍——有兩個問題在空氣中浮現,一是誰去洗碗,二是不同的人去洗碗會面臨不同的評判壓力。比如說,姐夫們當然不會去洗(父權問題按下不表),姐姐們也不會去洗因為會自覺是客人且比較年長,如果她們去洗,自己會感覺有一種社會輿論在評價她們「太卑微」。那就變成我去洗還是女友去洗,如果只有我們倆人,當然誰洗都不是太原則性的問題。但在那個情況下,我意識到,如果女友去洗,大概會得到以姐姐姐夫們為代表的社會輿論的「好評」(某種乖巧的性格?),但女友會對此很憤怒(她也意識到了這種社會壓力的存在,因此她非常淡然地把碗給了我)。最終當然是我去洗,而我順理成章地得到了社會輿論的「差評」(太嬌縱女友?)。
是不是應該算清楚呢?最近聽說了一個app,叫做「Choreful」——挪威一個程序員丈夫在一場關於家務的吵架後寫的。這位丈夫不常做飯,有一天下廚了,就想著妻子可以洗碗;可是累了一天的妻子吃完飯就拿了本書坐在了沙發上——他們吵了一架,不知道吵架誰佔上風,但顯然寫代碼很順手的丈夫回頭就去做了一個app,他要算一算到底誰做更多的家務⋯⋯很快,很多朋友們便來問他要一份拷貝,在男女家務分工號稱世界最公平的挪威,他們也想仔細算一算。
原諒我不厚道地笑咗,be supposed to 同埋expect to係有好大嘅距離,好多時其實係雙方都唔理解對方,而又冇任何一個人退讓;但如果有人肯褪後一步,就會好容易化解矛盾,知道對方究竟點諗
看不到「瑣事」裏的等級,又看不到這樣的「等級」是怎樣應用到其他以性別、種族、親疏等等排列的「身分」等級上,而其中又有哪裏矛盾重重、甚至充斥著(象徵)暴力的話,「洗碗性別為女」這種「小事」,一定還會延續非常久。
「娘相」是我們那個社會對男人最羞辱性的稱呼,意思是像女人一樣。這個社會對男人的認識和期待,是不要糾纏在女人做的事情裡,男人不需要在家灑掃應對,如果主動做這些,反而會遭遇阻力,因為男人應該從家裡消失,去外面賺錢。但我們那個社會又有大量沒有工作、遊手好閒的男人,他們也被認為應該從家裡消失,去外面尋找賺錢的機會,或者假裝扮演賺錢的角色。而家庭是虛位以待,等待這個消失的男人回來統治的,他一旦回來就變成飯桌的中心。這個中心在喝功夫茶的茶几上,男孩從小在家只被要求學會一種家務——泡功夫茶。泡茶意味著坐在客廳的中心位置,學會燒水,放茶葉,洗茶杯,鍛鍊出一隻耐受熱水的手,長幼有序地招呼客人。我從小被教導,不會泡茶就娶不到老婆,但現在顯然,不會洗碗才是問題所在。
自從我們一家跟隨我爸的工作搬到另一個城市後,我媽就變成了家庭主婦,已經有十二年了。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裏,包攬絕大部分家務活。她並不是不能出去工作,只是我爸總對她說「不需要」。有時在一些飯局上,她話裏話外也挺驕傲自己的「賢內助」身份。
但其實,我媽內心一直都存在着「弱者」的自覺和自卑。過去幾年,她每次在家庭聚會、朋友聚會上喝醉,回家後都會持續自言自語,唸叨「我好沒用」、「我沒能出去工作」,她覺得自己沒能替我爸分憂,替家庭多掙一些收入。家庭主婦這個身份,因爲無法產生金錢這樣看得見的價值,她對此耿耿於懷,也非常嫌棄自己。不過,這種內心的聲音只有在她喝醉的時候才會顯露出來。一旦到了第二天早上,她又重新進入了往日的「正常」秩序。
- 人類體温
在過去至少20年內,研究人員已經知道平均體溫其實更低,大約是攝氏36.56度,而人體溫度的正常範圍介於攝氏35.72度至37.39度之間。但擔憂的患者和醫生一直把37視為神奇數字,從藥局賣的溫度計到醫學中心網頁,到處都會出現它。
「醫生跟其他人沒什麼不同。」史丹佛大學的傳染病醫生茱莉.帕森內特(Julie Parsonnet)說:「我們從小就接受『攝氏37度是體溫正常值』的觀念。」
這種變化與帕森內特的理論一致,她認為人類代謝可能隨著時間逐漸減少,而且因為工業化國家的人民更容易取得食物和醫療照護,所以也會出現其他人體變化。
這種原始水銀溫度計有一支保存在費城的馬特博物館,馬科維亞克借了這支儀器來檢查。
「我們做了一些詳細的研究來檢查它的範圍,」馬科維亞克說:「〔它〕比現代或同時代的溫度計高攝氏0.83度。」
該研究提供另一個獨立資料集,顯示人類正在降溫。但如果這種現象是真的,目前也尚未找到明顯原因。古爾文說:「大家都有不同想法。」
其中一些可能原因包括空調、飲食、慢性疾病、免疫系統活動、牙科疾病、寄生蟲、睡眠習慣、抗發炎藥物。
體溫「只是疾病的徵象之一」。帕森內特說:「我們喜歡它是因為它是一個數字,每個人都喜歡數字……但事實上,無論你的體溫是多少,如果你覺得不舒服,你就是生病了。」
- 戲劇性氣候抗議

既然講到人嘅體温,就講埋氣候問題喇(雖然好似都冇乜嘢邏輯?)
如何引起更多人嘅關注同支持?呢種戲劇性嘅抗議方式確實比以前嘅其他方式更有效得多
不過壞消息係,呢種方式其實好難令到大眾可以持續地支持呢個議題,just like其他議題一樣,漲得快但又消失得快,如果冇辦法喺好短嘅時間內推動到政策嘅改變,噉樣喺長期入邊就同冇發生過冇太大差別——my point is,必須有人喺立法or提案嘅路上不斷推進,二者合一先有更大嘅機會
- 《金髮夢露》

夢露,是一個美國爲全世界所輸送的最重要的文化符號。作爲她的傳記電影,《金髮夢露》對夢露的影像作品的再次演繹,成爲了組織電影敘事的重要線索,也是散落在全片的謎語,等待被觀衆檢索。謎語是晦澀的,於是觀衆們爭論,對夢露那被風吹起的裙襬的反覆特寫,到底是對男性凝視的諷刺,還是對夢露的二次剝削?
多米尼克在接受《視與聽》採訪時這樣解釋重現夢露影像的意義:「她被困在我們對她的記憶中,想要掙脫出來。這是一部關於無意識的電影,我們和她知道的一樣多,因爲她的生活本質上是未經檢驗的。」以這句解釋作爲謎底,我們會發現自己錯過的線索:對男性凝視的呈現固然觸目驚心,卻並非敘事的最終目的。
不論是影像還是現實中,諾瑪·簡的追尋註定面對失敗:她從不曾作爲諾瑪·簡被真正看到。所有人看待自己的目光都是藉由夢露的銀幕形象建立:母親認不出雜誌裏的她,第一任丈夫視她爲蕩婦、第二任丈夫偷偷將她視爲可剝削的創作對象。她或許作爲夢露得到了虛幻的愛,但夢露的形象最終也會摧毀了她,她不斷成爲更美豔的夢露,對她的性剝削與傷害就不斷升級。這就是諾瑪·簡追尋的終點,這個世界給她的答案。
這個終點意味着夢露和諾瑪·簡的生命都要結束了,但這個答案也是諾瑪·簡拼盡力氣才得到的結果,她努力地去做一個真實的人,也努力地想要得到真正的愛,最終她得到了答案,一個毀滅性的答案,就是她所面對的世界存在結構性的問題,結構性的問題讓想要追求真實的人生與真實的愛的人毀滅。
通過瑪麗蓮夢露,觀衆完全拋棄了自己在凝視色情時的愧疚感,因爲夢露對凝視並不在意,反而包容與感激。這是電影史裏絕無僅有的,同時具有絕對的美與絕對的寬容的銀幕形象,觀衆利用了諾瑪·簡的創傷,與虛擬的銀幕一起合謀進行了剝削。
當好萊塢黃金時代最重要的電影作品被詮釋爲夢露的痛苦來源時,顯而易見,《金髮夢露》有別於《大飛行家》、《大藝術家》等沉迷於好萊塢傳奇的迷影電影——它立場鮮明地表達了其反迷影的立場。當攝影機調換視角,讓《金髮夢露》的觀衆從《紳士都愛金髮美人》的銀幕看向彼時的觀衆席,親眼目睹了諾瑪·簡的難堪與崩潰時,電影早已超越了對男性凝視的批判,而對自以爲可以袖手旁觀的影迷提出了問題:
當你在愛着瑪麗蓮·夢露時,你是否在對諾瑪·簡的痛苦視而不見?如果瑪麗蓮·夢露的銀幕形象成爲我們得以了解諾瑪·簡的全部介質,這樣的愛是真實存在的嗎?
在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自願」本身成爲了一種可以被所有人挪用的文字遊戲。製片廠時代對演員的控制是系統性的,性侵也是。在製片廠可以控制藝人的婚姻、性取向、發育、墮胎的前提下,並不存在「自願的性關係」。
銀幕上的演員是在飾演,而性侵的本質則是強迫,影像的虛擬本質決定了性侵的痛苦永遠不能被真正呈現。而當觀衆討論銀幕是否放大了夢露的痛苦時,是否意識到夢露是一個在寄養家庭被屢次性侵、十五歲爲了離開孤兒院而嫁給鄰居,在三十六歲意外自殺離世的女性?銀幕只是在試圖接近或扮演將悲劇,但真實的傷痛是發生在夢露的生命經歷裏的——觀衆無法真正感同身受,這或許才是應該焦慮的問題。
在「軟弱即爲失敗,失敗即爲矮化」的評價體系裏,受害者本身成爲了一種貶義詞,於主流價值觀判斷所不容的消極與失控,則成爲了受害者失敗的象徵,受害者必須要表現的正常才意味着反抗,其行爲的判斷標準依然由健全又幸運的人賦予——唯有鬥爭的話語才算反抗,唯有事業的奮進才算勇敢。
然而諾瑪·簡的人生無法承載這樣價值判斷單一的幻想:她的精神問題嚴重影響了事業,最終還是走向了自我毀滅,死亡時她的房間如同一片雪洞,甚至沒幾件傢俱。很難說她從「成功」裏得到了什麼回報,又對物質世界有什麼留戀。
這是一個悲劇的人生,但並不意味軟弱,追求自我常常導向自我毀滅,這是殘酷的世界給想要答案的人的回應。
在女權主義已擁有廣泛討論基礎的今天,《金髮夢露》卻因爲其人物的痛苦與毀滅遭遇了廣泛批評,其中正暗藏了當女權主義被消費主義所裹挾時必然會呈現的傾向:當追求個體真正自由的可能性被外部條件不斷打擊時,性別研究的公共討論與成功學劃上了等號——人們更願意從主義中找到成功的偶像作爲自我的投射,而不是從中看到痛苦與問題。
當女權的話語體系與價值判斷被傳統的父權標準同化,贏是成功的證明、成功是勇敢的象徵、脆弱與失敗劃上等號,被認爲是消極與可恥的存在,人們再難從中找到顛覆父權結構的武器,以自身感受去定義世界。
至少,即使是最終失敗的人,也應該有賦予自己行爲以意義的權利,正如夢露也堅持了很久。如果粗暴地貶低了痛苦的意義,她與痛苦應對的過程則不配被視爲一種反抗,我們忘記了痛苦的前提是有人在感受,而感受本身也是一種艱難的承受。事實上消極的行爲同樣也可能是反抗方式——當夢露知道片場的人不尊重自己時,她總是以遲到應對,雖然這搞砸了她的事業,但走到片場本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歸根結底,夢露是最早的明星,最早被大衆流行文化消費的女性,她的生活是未經檢驗的,和今天的我們一樣也只能摸索,她沒能給出一個完美的答案,因爲反抗從來也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化的路徑。「Girls help girls」,一個運動的主題並不總是如這些口號一樣激昂與歡快,女權運動並不意味着每個人都得到救贖,它充滿了力有不逮與追悔莫及的時刻,諾瑪·簡的存在,她三十六年的短暫生命就提醒了我們曾有過這樣的挫敗。
終其一生,夢露追尋着另一種人生,可在無盡的失敗與苦澀相聯的間隙,她依然有着期待、天真的時刻,依然願意與他人建立聯繫,就像那些痛苦從未存在、她不曾受到傷害一樣。在那些追尋的瞬間,她早已抵達終點,卻未曾察覺——在現實世界裏,直到夢露死去,無數女性打電話說如果她們知道夢露真實的處境,一定會更早去幫助她,在那時,她終於重新成爲了諾瑪·簡,一個被愛的女孩。
作爲影迷,夢露帶給了我迷影的幸福,但作爲女性,我更希望能愛她的失敗與痛苦。
- Mobile Gamb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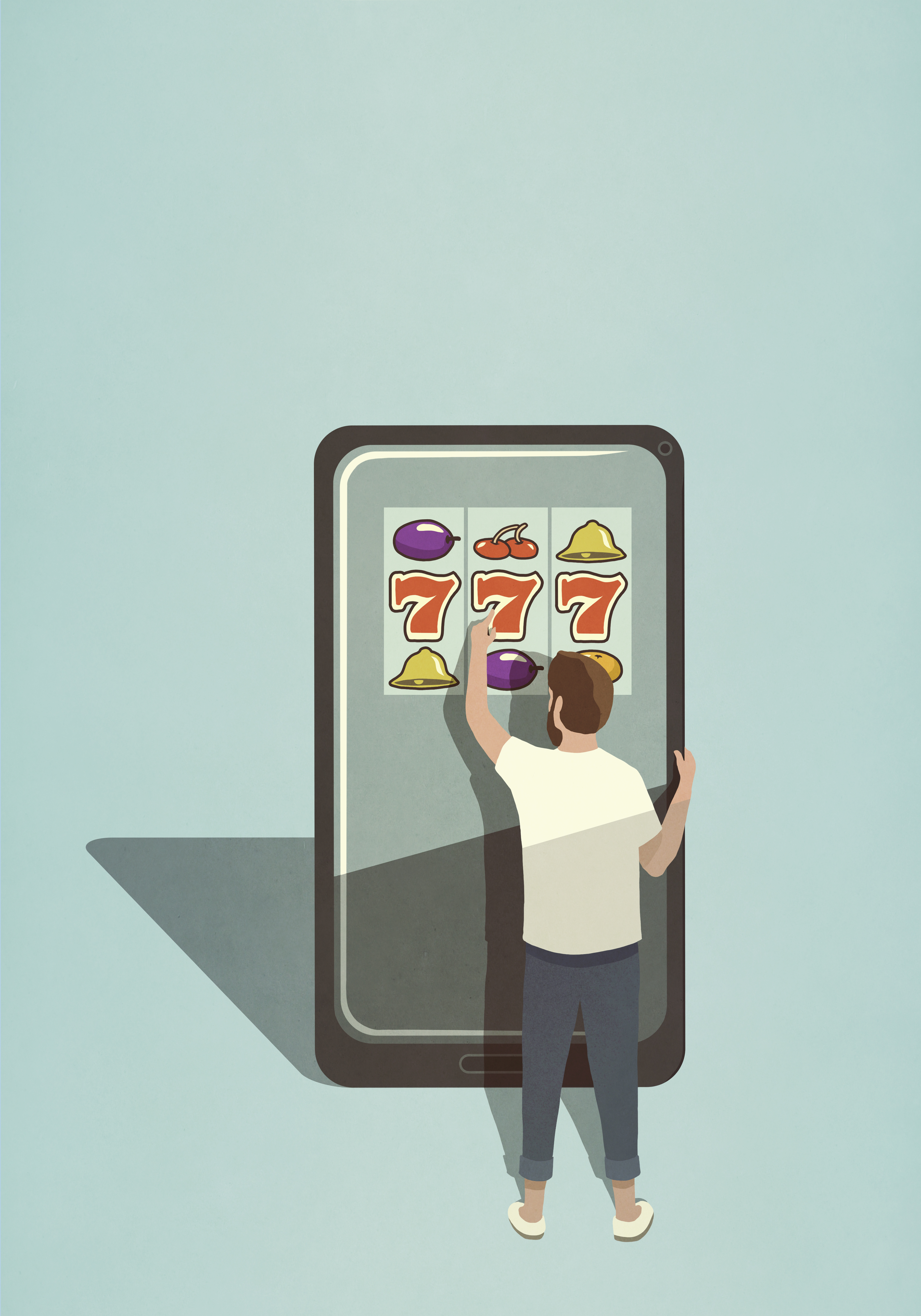
unstoppable,只要有利可圖,就好難禁止,而最攞命嘅就係而家可以直接喺 online 賭博,就更加難以發現同埋上癮,但係,十賭九輸,即使好彩賺到少少錢都會好快輸返——所以呢個完全就係好壞嘅癮
Regardless of the legality, the growing prevalence of gambling in society helped him legitimize his habit to himself. It felt less “seedy,” he said, even if he would gamble until three in the morning while his kids slept “and then wake up and do it again.” By this year, Jason didn’t go a day without gambling.
“It's pretty conclusively established in the gambling literature that ease of access is a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ambling problems,” Whyte said. “Ease of access alone doesn't make doesn't make someone a gambling addict. But it certainly can contribute to an increase in the rate and severity.”
Since he stopped gambling in May, Jason has noticed with fresh eyes just how prevalent the gambling industry has become. Nationally, entire sports shows are now dedicated to gambling, and others don’t go long without mentioning an exciting potential parlay bet. Gambling commercials play all the time on the radio and when he watches sports, and the leagues themselves have signed official partnerships with companies like FanDuel and DraftKings.
“It is everywhere now,” Jason said. “It's kind of disgusting when you start to look at it from the outside in.”
- 台灣經濟

然而吳聰敏亦提醒,換算成美元的名目GDP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只要匯率大幅升貶,GDP數值也會跟著波動。以台幣為例,2017年初,一美元兌台幣約32.2元;到了2021年底,台幣匯率則來到了27.6元左右,五年來升值了約14%,幾乎創下25年來的新高。
「比較好的衡量方法,其實是看拿到所得之後,究竟可以換到多少東西,所以GDP計算才會發展出所謂的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購買力平價)。」吳聰敏指,若根據PPP計算,台灣的人均GDP其實已經將近60,000美元,不僅接近荷蘭的水平,也高出台灣的名目GDP非常多。
若以PPP計算,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台灣的人均GDP排行,在世界上人口多於兩千萬的所有經濟體裡,甚至高居第二,僅次於美國。
值得注意的是,水電、教育、醫療支出,在台灣確實都是受政府高度補貼的項目;此外,PPP僅考慮房租支出,並沒有計算購屋的房價,未必貼近台灣高房屋自有率的文化,而在房價高企的台灣,也可能低估了台灣人的生活支出。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受僱員工薪資調查」,2020年台灣的年薪中位數為50.1萬台幣(約14萬港幣,11.5萬人民幣),代表台灣約800萬受薪勞工裡頭,有半數人的年薪不及這個數字。若與2012年相比,薪資中位數八年來只成長了13.35%,然而人均GDP在同個期間,卻成長了33.1%。
若以「平均月薪」計,台灣2020年的平均月薪為54,160元(約15,245港幣,12,461人民幣,和八年前相比,只成長了17.46%,同樣大幅低於GDP漲幅。
吳聰敏指出,台灣這波經濟成長,主要仍與台灣外銷暢旺、國際間對台灣電子產品的需求有關,所以各個行業的勞工,分配到的經濟成長果實,其實差距頗大。
林宏昇的說法,也再次印證了一件事:高收入的群體,對風險的耐受度也更高,也因此更有機會在牛勢的資本市場裡獲利,近一步拉開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
不過若和大部分國家相比,台灣的貧富差距其實仍不算嚴重:從吉尼係數來看,台灣近二十年來一直都維持在34左右,貧富差距並沒有出現顯著惡化。
若引用「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統計,也能得到相似的圖像:收入排行前10%的台灣人,掌控了約36%的整體收入,和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狀況接近;相較之下,同個數據在香港將近49%,美國、韓國、日本大約都是45%,中國大陸則是約42%──換言之,收入集中於有錢人手中的情況,在台灣其實相對不那麼嚴重。
所謂的GDP,中文一般稱「國內生產毛額」,指的是一段期間裡,一個經濟體裡所有生產活動的「最終產值」總額;為了避免重覆計算經濟活動,每個生產活動都必須減掉「中間投入」──用白話說就是,除了領薪水的勞工之外,所有營利事業的營收,也都必須扣掉物料成本、人力支出,只計算每個生產活動的「附加價值」。
許多人容易誤把「所得」等同於「薪資」,但實際上,一個經濟體的GDP,並非只由勞工的薪水組成,也包括企業雇主的利潤;而不事生產,靠房租、利息、股息過活的「食利者(rentier)」,他們的房租或利息,也會計入GDP之中──換言之,除非一個經濟體不存在任何地主跟股東,否則平均薪資本來就不可能等於人均GDP。
就經濟展望來說,台灣近年的經濟榮景,是受益於疫情和電子產品的需求,然而一旦這個因素消失,榮景是否便會無以為繼呢?儘管產業界一般預期,晶片短缺問題短期之內不太可能解決,但過度仰賴半導體產業、以及其他電子業出口,作為主要的成長動能來源,長期來看,究竟是否健康呢?
說到底,GDP數據和排行雖然粗描出了台灣經濟的整體圖像、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但終究不是事實的全貌,而台灣經濟的其他挑戰與問題,也終究不是單憑人均GDP數據,就能夠輕易解答的。
- 青年選里長

郭書成表示,318學運使他發現,自己也有改變社會的機會,於是萌生參政念頭。學運時正休學服役的他,役期結束後回到母校國立中山大學,透過擔任學生會會長累積經驗。
畢業後,他想避開政黨包袱,自主參與民主;同時,他發現從小居住的伯爵山莊,由於缺乏維護,建成多年後公用設施出現問題,如自來水系統不時停水、籃球場地板破裂和泳池停運。不忍社區變得破敗蕭條,他投入2018年的地方選舉,參選伯爵山莊所在地的新北市汐止區湖興里第13屆里長。
從參選開始,他就把前衛做法帶進社區,不想以人情來爭取選票,郭書成採用政見取勝。早上拜票時,他不鞠躬,轉而用白紙板寫下「早安!您好!我是郭書成」、「我會用新方法解決舊問題」,再附上臉書粉專名稱,邀請選民追蹤和了解他的政見。
面對選民與前任里長的人際包袱,郭書成沒有勉強硬碰。他選擇開發新票源,成功爭取到足夠的年輕選民支持,以25歲的年齡成為湖興里歷來最年輕里長。
今年年底選舉有超過3,000個村里別將只有一名候選人,同額競選的情況比往屆更普遍。同時,「青年參政」的概念在媒體報導下,已不是八年前的改革理想;如今青年參政,個別「最美」、「最帥」里長的聲浪已蓋過熱血願景。郭書成觀察到,參選人數降低是因為村里長的職位,沒有給人很大的參選誘因。據他觀察,「現在政治越趨保守,資本也更集中,變成有更多政二代出來,新人很難出頭。」
王時思則將「獨立村里長學院」視為替村里長這份公職「除魅」的方式,「公僕這個概念殺死人。如果是僕人的話就要服從主人,但公共事務需要雙向溝通,但是公僕的概念奪去了工作的尊嚴和回饋。」回歸工作本身,王時思希望得以重建村里長和選民的平等關係。
或許有人覺得投了票給村里長,村里長就有義務處理所有社區鄰里大小事。不過,王時思認為即便如此,村里長也難以自行提出解決公共事務的方案。「沒有哪一種授權,可以交給村里長後就完全不管,」她解釋社區議題的決策仍然需要公共合議,「沒有空白的授權,而必須透過參與、決策,以決定授權的方式和範圍。」
她期待社會不再用階層化來看公共事務參與,要讓每個位置都有獨特的價值。她說,不是對年輕人說「好可惜喔,你318那麼厲害,現在怎麼只來選里長」,而是鼓勵他說「你很棒」,願意在地服務,成為共同生活的推動者。「這個人也用不著承諾這是一輩子的事情,這可能是職涯規劃裡面中的一段,但會因為這一段,促進台灣島上共同生活的可能跟想像。」
學運啟蒙青年八年後,或許是時候打破神聖公僕的迷思,讓村里長這份公職,不只燃燒使命感,也回歸工作的本質。相較透過理想去從事一份工作,不若從事一份工作,從中實踐理想。
- Little Rituals

little non-negotiable things help us keep going
my version: read book? exercise? or play smartphone...(please ignore it
- 美國中期選舉催票議題

經濟向來是民主黨的軟肋,華爾街和蓋洛普(Gallup)民調共同指出共和黨向來被視為更有能力解決經濟問題、提出有效經濟政策,尤其在抑制通膨上,對共和黨的信心更是高於民主黨超過十個百分點,共和黨也聚焦經濟,競選廣告主攻民主黨在經濟議題上的挫敗與負面形象。隨著經濟問題持續作為民主黨選情最大敗筆,目前可以觀察到民主黨逐漸改變經濟論述,從原先傾向提高企業與富人徵稅、建立更平等的社會網絡,在部分政策轉向大企業靠攏,尤其在搖擺州特別明顯。
目前民主黨持續利用墮胎議題翻轉在經濟議題上的頹勢,而在短時間無法聚集黨內墮胎立場的同時,共和黨則將中期選舉的焦點,聚焦於有利於該黨的犯罪問題。
- 「中國式家長」
中国式教育中,亲子矛盾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父母想让孩子好好学习,孩子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双方都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父母和孩子会越来越无法理解彼此,游戏制作团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这款游戏让有孩子的父母可以审视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让孩子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待成长问题。
“按摩技师和流水线工人,是我们设置的两个保底职业。”杨葛一郎说,“但这两个保底职业,我们会安排相对温暖的人生,因为我觉得,在各行各业,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发光发彩。”
玩来玩去,最终还是对结局不满意,才会有很多的执念,继续玩下一代。现实也大抵如此,这时候很多人就能理解父母当年对自己的那些期望和压迫了,因为“父母希望孩子是自己人生的延续”。
这与杨葛一郎后来发现的现象相吻合。他注意到,《中国式家长》的玩家,相当一部分都是学生。他们往往是中国式家庭的被迫害者,在游戏里想体验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与父母期望相反的人生。而另一些人,则会以上清华北大为目标,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顺应“中国式父母”的期望,感受一个学霸带来的体验,以至于出现了非常多“如何上清华北大”的游戏攻略。
游戏跟现实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游戏里的“代际”设定,只要你一代一代地玩下去,就永远有选择的可能。
在游戏里玩家可以通过两小时一代人的苦心经营达成最终的完美结局,但现实中的普通人甚至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掌控,只能背负着上一代人的期望与遗憾前行,再把自己的期望与遗憾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在中国式的家庭里长大,最后成为中国式的家长。
人们的现实人生,终究没法像游戏里那样,能够重来一遍。而关闭了游戏,所有人都要回归现实。
- Why Socrates Hated Democracy
download from The School of Life| Why Socrates Hated Democracy
Socrates’s point is that voting in an election is a skill, not a random intuition. And like any skill, it needs to be taught systematically to people. Letting the citizenry vote without an education is as irresponsible as putting them in charge of a trireme sailing to Samos in a storm.
We have preferred to think of democracy as an unambiguous good – rather than as something that is only ever as effective as the education system that surrounds it. As a result, we have elected many sweet shop owners, and very few doctors.
係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知識分子民主同生來就有嘅民主確實有好大嘅唔同,and 前者同精英政治又有所唔同——vote 係要嘅,唔應該所有人都有。而除咗要經過教育、訓練實踐之外,其他限制就唔需要有了
- 普通人喺極權社會

關於人的處境,套用馬克思的描述,“人類創造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無法隨心所欲創造人生,也無法按照自己選擇的環境來創造人生,只能依據直接遭遇到的,源自過去並延伸至今的環境來創造人生。”既然我們無法回到過去,扭轉造成今日處境的決定,同時還要在按現實環境創造人生,我們只能依靠自身的判斷力來作出良善的選擇。
政治權利和義務失衡的天秤上,作為單數而且是孤島的個體,還須抱有怎樣的心態,在所有表達異見渠道已遭封閉的極權社會里自處?上述討論或許是一種參考。最後,東、西方文化裏有句相近的諺語,可以成為公共政治生活的旁依。不論是蘇格拉底的“寧受不義而不作惡”,或是《論語》裏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者放在公共倫理都要求個人要換位思考,從他人的角度去設想自己行為的後果,並視之為行事和判斷善惡的準則。極權社會里每個人都是孤島,但至少面對這無力感時,個人的回憶、思考和判斷已成唯一不受外力干擾的行動,好讓我們保有基本人性,而非單純淪為盲目服從歷史法則的齒輪。
- Iran Protests

拉嘅人均15歲…… so sad. 奮不顧身孤注一擲嘅感覺,弱小血肉之軀,意志同決心卻好 firm,真希望可以成功
- 四通橋抗爭

當然,政府有足夠的理由擔心零星的模仿者會導致事態的擴大,但即使事態真的發展到「群體性事件」的地步,國家機器仍然掌握着強大的暴力權力——正如1989年6月的新聞播音員所說:「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當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然而另一方面,這次孤立的、沒有形成群體行動的個人抗議,卻又似乎的確觸及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本問題。在政治學中,有一個長久以來困擾研究者和觀察者的問題:如果強大的國家機器可以用暴力壓服一切反抗,它爲何還需要深入介入人們一言一行的意見表達?換句話說,如果坦克可以踏平六四事件那樣大規模的抗議人群,爲何中共仍然會爲一次「孤狼」式的抗議標語而膽戰心驚?
事實上,像中國政府一樣,細緻審查和管理人民的每一次意見表達,在威權國家之中,是少見的。即使號稱強硬的俄羅斯普京政權,在言論管制和意見表達上,也遠遜色於中國,不僅給大規模抗議行動留下了空間,像四通橋事件這樣的孤狼式抗議更是家常便飯。這部分是因爲,即使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家權力和對社會的滲透程度也沒有達到中國的程度。
但更重要的是,細緻地管理人民的一言一行,對於政府的精力支出和收益而言,是不划算的。如果政府的終極目標只是掌握政權,保持權力,則不必在孤立的意見表達上大做文章。幾年前,在中國研究領域,也曾經出現過一個頗爲主流的理論,認爲中國的言論審查,都以阻止群體性事件爲主要目的;如果不會形成危及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則審查並不會十分嚴格。
本質上,中國共產黨無法從西方一般理解的「民意」或「輿論」(public opinion)中獲取合法性。這種西方意義上的「民意」,來自於多數的授權,來自於對支持與否的量化。但中國共產黨的「民意」是不能量化的,因爲「人民」是一個被召喚出來的抽象概念,只有全部而徹底的民衆支持,才能夠滿足共產黨對其合法性的宣稱,因爲哪怕少了百分之一、萬分之一,也不是「全體人民」了。
這種整體觀念是中共的優勢所在,卻也是其巨大的弱點。其優勢在於,只要「共產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假象仍然存在,中共的任何行爲都可以不計後果,可以將社會隨意宰割。它可以聲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句話意味着,它不需要對真正的人民負責,因爲它自己就是「人民」。
但另一方面,它必須時刻如坐鍼氈,因爲只要有一點反對的聲音出現,它的統治基礎就稱不上牢固。
如果沒有人發聲,即使有多於50%的人反對,反對者也仍然是零,中國政府的支持者仍然是「全體人民」;但如果不斷有人發聲,即使還有多於50%的人支持現政權,政府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聲稱自己代表了全部十四億人。
因爲這一層邏輯存在,每一次被傳播出來的反對聲音,即使從實際的政治權力角度而言或許並無巨大影響,但卻都是在動搖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根本。如果中國不能順理成章地宣稱自己就是「全體人民」、代表了人民的總體意志,中國最終將淪落爲與俄羅斯、伊朗一樣,只依靠暴力進行統治,而不再身披華麗的合法性外衣。
當然,這絕不意味着利維坦就會失敗,因爲即使只依靠暴力,中國政府仍然具有哪怕俄羅斯也無法比擬的強大強權。但如果能夠繼續不斷出現零星的「輿情事件」,哪怕不是四通橋這樣直接觸碰政權本身的事件,也仍然意味着戳破「全體人民的意願」這一神話的希望。
- 離開與留低
革命失败后,米克洛什·克劳绍和我表弟帕尔·扎多尔告诉我,他们会在第二天离开,叫我跟他们一起走。他们保证我能通行。他们给我看了,文件上有我的名字。他们的故事是,我们要去劝其他人回家。
我拒绝了。我说,事情不可能比之前更糟了。我会坚持的。我会活得比领导者久。我不想卷入这场大外流中,我想要了解这里、这些街道上发生着什么。这是个未完的故事,我拒绝从中脱身。
如果我走了,我会去哪里呢?人们朝着不同方向离散,但这仍是我能找到最多说匈牙利语的人的地方;我能最为轻松地生活,适应街道、语言和习俗。然而我支持他们的离去,因为我怀疑,跟我相比,他们留下来会遇到更大的危险。他们不太能继续在这里生活,因为他们比我更活跃、更坦率直言、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更重要。我只不过是个乱出主意的人,一个武装的旁观者。
每个离开的人都是对的,每个留下来的人同样如此。每个人都试着注意命运的提示。我给自己的建议是:只要不处于致命威胁中,就挺直腰板。继续前行,但不要太匆忙。你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冲动决定。继续安静、踏实、不起眼、持续地工作。
我没有在1956年离开。每次机会现身,我都坐在桌前写作。每当需要做出特别重要的决定时,我都会停顿下来,让事情按照原计划发生。更有活力的人离开了;剩下的人坚持到底,在磨炼中成形。当我从远处想起他们时,我喜欢他们;当我遇见他们时,我尽可能溜走。
尽管我留了下来,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个现实和噩梦的黑暗钟罩,那个直面焦虑的空间,会很快再次扣到我身上。这时候应该学习与忧虑同居,同时又确保它不喧宾夺主。1956年后,人们不再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想法。“五六”年精神转身面壁,并拉过毯子盖住耳朵。大多数记忆消亡了,保持它们鲜活毫无益处。
事实上,有时候我害怕知道自己后天会想什么。我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连续好几年的生日都只提醒了我,在革命之后愚蠢的五年里我有多少事未能完成。
在冗长废话的汪洋里偶遇坚实岛屿,总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在审查盛行之年阅读有实质内容的作品是一种避难,是对那些挤进家中的谎言的暂停。包里有一本好书,是对我不得不忍受的陈词滥调的补偿。我们可以用文学苛责人们,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学会了阅读,就能用它来原谅他们,并为他们的美丽而着迷。自从文理中学时期起,我就相信,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文本的持续讨论维系着人类的进步。
- 「外婆」vs「姥姥」

算笑死,理鬼你原文係點,話你方言就係方言,方言就係要換成普通話!
噉請問要唔要換晒走啲古文?仲有古詩嗰啲呢?甚至話一啲課文嘅方言?好似有啲文章都係有京話兒喎?
- 蔡雲峰

always 財新,可惜發出嚟冇幾耐就 404 咗……分享呢篇文章唔係腐敗問題——因為呢個已經係體制結構問題,完全唔出奇,只係悼念一下呢篇文章
- 《小熊維尼》真實世界

對米恩來說,《小熊維尼》的爆紅,反而凸顯出他生命中的一種遺憾,那就是他雖名滿天下,卻無法以嚴肅作家的身份為世人所知。而對克里斯多福.羅賓.米恩來說,《小熊維尼》為他帶來的遺憾,恐怕要比他父親所經歷的遺憾更為深沉。羅賓在晚年出版的自傳《魔法之地》(The Enchanted Places)中,曾寫下這樣一段令人感到沉痛的話:「在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時間裡,我都對小熊維尼懷有怨恨。」
我認為《小熊維尼》最美好的地方,在於百畝森林裡的所有動物朋友們,當他們耍笨時,他們都是如此坦然地面對自己的無知。
在成年人的世界裡,每當我們內心惶惑、手足無措時,我們總要裝出一副鎮靜、沉穩的樣子,不能讓人看出我們的無知,不能讓人看出我們內心的慌張。但是克里斯多福.羅賓和所有百畝森林裡的動物朋友們,從來不會去掩飾自己的錯誤,也從來不會去掩飾自己的笨拙,而且也從來沒有人會去嘲笑他們。
- Best-seller novelist

really good, 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寫自己想寫嘅題材,why not?唔一定要侷限於一個方面,同埋有時火爆都幾難解釋,名聲唔一定係好東西,and 平常心地去面對,當佢好快就過去,繼續享受當下
Her success has happened largely on her terms, led by readers who act as her evangelists, driving sales through ecstatic online reviews and viral reaction videos.
Her fans, who are mostly women, call themselves CoHorts and post gushing reactions to her books’ devastating climaxes. A CoHo fan who made the following plea on TikTok is typical: “I want Colleen Hoover to punch me in the face. That would hurt less than these books.”
Most blockbuster authors break out because of a popular series, like “Twilight” or “Harry Potter,” or build a brand by writing in a recognizable genre. Hoover is eclectic. She’s written romances, a steamy psychological thriller, a ghost story, harrowing novels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drug abuse, homelessness and poverty. Though her books are hard to categorize, most of them have an addictive combination of sex, drama and outrageous plot twists.
“I kept being told that authors need to brand themselves as one thing. And I was like, well, why can’t I brand myself as everything?” Hoover said. “Why can’t I just brand myself as Colleen Hoover?”
Hoover, who says she suffers from “the worst case of impostor syndrome in the world,” seems bewildered by it all.
“I read other people’s books, and I’m so envious. I’m thinking, ‘Oh my God, these are so much better, why are mine selling the way they are?’” she said.
“It’s not me,” she continued. “The readers are controlling what is selling right now.”
“Her writing helped me laugh, cry, fall in love,” she said. “The books helped me learn how to feel again.”
Fame has come as a shock to Hoover, who is almost painfully introverted, and dislikes being in the spotlight. “I’ve been so nervous about this,” she said about participating in this article. “I don’t do well with interviews.”
She still shops at Walmart in her pajamas, and lives on the same 100-acre plot of land where her family’s farm used to be. Her uncle still harvests hay for his cattle on the property.
As her audience has grown, Hoover has struggled at times to maintain her close connection with her readers. After the romance convention, Hoover heard complaints from some volunteers and friends who felt slighted. Hoover cried on the drive home, and called her mother.
“She was like, ‘You know what, Colleen? This is the trade off,” Hoover said. “And I was like, you’re right. You know, I’m very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that’s happening with my career. It’s also scary.”
Just as she never expected to be a best-selling author, she said, she doesn’t expect it to last.
“Still, in my head I’m like, ‘This is going to end tomorrow,’” she said. “So I need to enjoy it.”
- 輿情「王牌小編」

well……真係當睇戲噉睇。人死咗,就真係冇噶喇
同埋果然邊度嘅政治都係一樣黑暗同官僚落後……
- 外交官分析俄羅斯
俄罗斯非法行为的源头——来自一名脱离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官 | 《外交事务》
多年来,俄罗斯外交官被要求与华盛顿对抗,并以谎言和转移话题的方式为该国的海外的干涉行为辩护。我们被教导要接受轰轰烈烈的言辞,并不加批判地将克里姆林宫对我们说的话转述给其他国家。但最终,这种宣传的目标受众不只是外国;而也是我们自己的领导层。在电报和声明中,我们被要求告诉克里姆林宫,我们已经向世界成功推销了俄罗斯的伟大,并摧毁了西方的论点。我们不得不避免对总统的危险计划提出任何批评。这种表现甚至发生在外交部的最高层。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多次告诉我,普京喜欢他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因为他工作起来很“舒服”,总是对总统说“好”,告诉他他想听的话。因此,普京认为他能轻易打败基辅一点也不奇怪。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军事工作的人来说,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并不像西方担心的那样强大,这要归功于西方在俄罗斯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后实施的经济制裁,这些制裁比它们的制定者似乎意识到的更加有效。
许多苏联公民相信,当他们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西方会帮助他们。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天真的。西方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许多居民——以及一些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解决该国巨大的经济挑战所必需的援助数量。相反,西方鼓励克里姆林宫迅速取消价格控制,迅速将国家资源私有化。一小部分人通过抢购公共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非常富有。但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所谓的休克疗法导致了贫困化。恶性通货膨胀袭来,平均预期寿命下降。这个国家确实经历了一段民主化的时期,但大部分公众将新的自由与贫困等同起来。作为结果,西方在俄罗斯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在北约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行动之后,西方的形象又受到了重大打击。在俄罗斯看来,这些轰炸不像是保护该国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行动,而像是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受害者的侵略。
感覺呢,其實俄羅斯人一直都幾天真,最近嘅就係喺二戰時就提出要同英美結盟抵抗德國法西斯……嗰時同樣因為意識形態嘅問題過咗好耐西方先同俄羅斯結盟
我注意到有几个错别字,就告诉他我会纠正它们。“不要这样做!”他回击道。“我们直接从莫斯科拿到了文本。他们更清楚事情。即使有错误,也不是由我们来纠正中央。”这体现了该部将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对领导人不加置疑的敬畏。
在我的同事中,对吞并克里米亚的反应从混合到积极不等。乌克兰正在向西方漂移,但这个省份是普京对历史的混乱看法有一些依据的少数地方之一:克里米亚半岛于1954年在苏联境内从俄罗斯移交给乌克兰,在文化上更接近莫斯科而不是基辅。(超过75%的人口将俄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迅速和不流血的接管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引起抗议,在国内也非常受欢迎。拉夫罗夫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发表演讲,将俄罗斯的行为归咎于乌克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我和许多同事认为,普京将克里米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更有战略意义,我们可以尝试将这一行动包装得没那么有侵略性。然而,普京的工具箱里不存在低调的手段。独立的克里米亚不会给他带来收集齐“传统”俄罗斯土地的荣耀。
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建立一个分离主义运动并占领该地区,更让人摸不着头绪。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2014年的前三年,没有像吞并克里米亚那样在俄罗斯引起大量的支持,而且还招致了另一波国际上的责难。许多部里的员工对俄罗斯的行动感到不安,但没有人敢向克里姆林宫传达这种不安。我和我的同事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普京夺取顿巴斯是为了让乌克兰分心,防止该国对俄罗斯产生严重的军事威胁,并阻止其与北约合作。然而,很少有外交官(如果有的话)告诉普京,通过助长分离主义分子,他实际上将基辅推向了他的克星*。
个健康的外交部旨在为领导人提供对世界不加修饰的看法,以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尽管俄罗斯外交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包括一些不便的事实,以免他们的上司发现有内容被省略,但他们会把这些真相埋在堆积如山的宣传内容中。
我一直希望我的同事们能私下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表示不安,而不仅仅是感到困惑。但许多人告诉我,他们完全满足于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逃避对俄罗斯行动的责任的方式;他们可以通过告诉自己和其他人,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能理解这一点。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人对我们越来越好战的行为感到自豪。有几次,当我提醒同事们,他们的行为太粗鲁,无法帮助俄罗斯时,他们会提及我们的核力量。“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人对我说。他继续说,其他国家“必须按我们说的来”。
也许有几打外交官悄悄地离开了部里。(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一个公开与莫斯科决裂的人。)但大多数被我视为有理智和聪明的同事都坚持留下来。“我们能做什么?”一个人问。“我们是小人物。” 他放弃了为自己提供理智的思考。他说:“莫斯科的人比我们更懂。”其他一些人在私下谈话中承认这种情况的疯狂。但这并没有反映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继续散布关于乌克兰侵略的谎言。我看到每天的报告都会提到乌克兰不存在的生物武器。我在我们的大楼里走来走去,实际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个外交官都有私人办公室,我注意到,即使是一些聪明的同事,他们的电视上也整天播放着俄罗斯的宣传片。仿佛他们正在努力向自己灌输思想。
外部分析家可能喜欢看俄罗斯经历一场重大的国内危机。但他们应该三思而后行,支持国家的内爆——不仅仅是因为这将使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落入不确定的手中。大多数俄罗斯人处于一种棘手的认知,这是由贫穷和大量的宣传带来的,这些宣传播下了仇恨、恐惧,以及同时存在的优越感和无助感。如果国家分裂或经历经济和政治灾难,就会把他们推过边缘。俄罗斯人可能会团结在一个比普京更好斗的领导人身后,挑起一场内战、更多的外部侵略,或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乌克兰赢了,普京倒下了,西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施加羞辱。相反,它是相反的:提供支持。这可能看起来有悖常理或令人厌恶,任何援助都必须以政治改革为重要条件。但俄罗斯在输掉比赛后将需要财政帮助,而通过提供大量资金,美国和欧洲可以在普京之后的权力斗争中获得筹码。例如,他们可以帮助俄罗斯受人尊敬的经济技术专家之一成为临时领导人,他们可以帮助该国的民主力量建立权力。提供援助还可以让西方国家避免重复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当时俄罗斯人感到被美国欺骗了,而且会让民众更容易最终接受失去帝国的事实。然后,俄罗斯可以制定一个新的外交政策,由一群真正的职业外交家来执行。他们最终可以做到这一代外交官所不能做到的——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诚实的全球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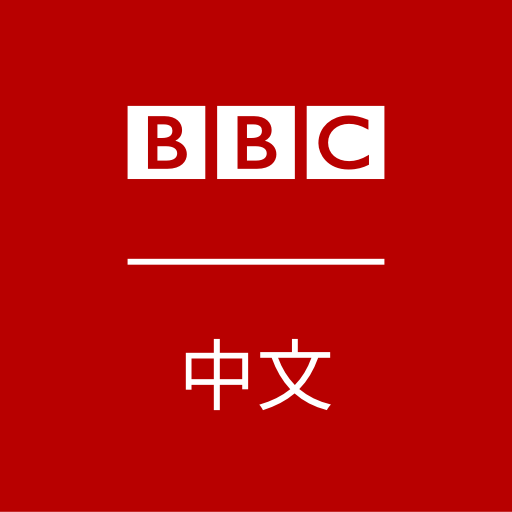


評論留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