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刊
地名;以巴戰爭;Loneliness;周庭;北上消費潮;OpenAI & Microsoft;白紙一週年;醫學實驗室;the Sun;啤酒館嘩變;gambling;歐洲中文書屋;翻譯;殘障歧視;
- 地名

學下地名點讀喇!都幾得意,雖然只係學到一個唔識嘅輋,不過都學到啲文化同歷史,幾好
- 以巴戰爭
There’s a single formula that can maximize the chances that the forces of decency can prevail in all three. It is the formula that I think President Biden is pushing, even if he can’t spell it all out publicly now — and we should all push it with him: You should want Hamas defeated, as many Gazan civilians as possible spared,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of Israel and his extremist allies booted, all the hostages returned, Iran deterred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n the West Bank reinvigorated in partnership with moderate Arab states.
呢個係最理想嘅情況,實際上發展到點都幾難預知
Unfortunately, as Haaretz’s military correspondent, Amos Harel, reported on Tuesday, Netanyahu “is locked in by the extreme right and the settlers, who are fighting an all-out war against the idea of any involvement of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n Gaza mainly out of f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will exploit such a move to restart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push for a two-state solution in a way that will require Israel to make concessions in the West Bank.” So Netanyahu, “under pressure from his political partners, has banned any discussion of this option.”
我哋最好唔好低估咗一個權力者維護自己嘅決心
1. The keystone for winning all three wars is a moderate, effective and legitimate Palestinian Authority that can replace Hamas in Gaza and be an active, credible partner for a two-state solution with Israel and thereby enable Saudi Arabia and other Arab Muslim states to justify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the Jewish state and isolating Iran and its proxies.
2. The anti-keystones are Hamas and Netanyahu’s far-right coalition, which refuses to do anything to rebuild, let alone exp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s role.
3. Israel and its U.S. backer cannot create a sustainable post-Hamas regional alliance or permanently stabilize Gaza while Netanyahu reigns 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一旦進入了「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情緒變得非常簡化。當人們只能想到生存,便看不見情況的複雜性,只能被恐懼或憤怒所驅動,沒有辦法反思。我現在試著透過書寫,讓人們了解現實比主觀經驗更複雜。
我的因應方式是,開始藉由寫作來逃避身處的環境,值班時我會想著我不在這裡,我在台灣、我在騎著龍、我在看著夕陽⋯⋯逃離到想像的世界,是我從納粹大屠殺倖存的父親身上學來的。他總是對我說,當被困在你不想要待的地方時,你的心中總會有扇門,打開門,總會有另一個房間,如果在牆上找不到,去你的內心找。這引領我進入創作與書寫的世界。
對我而言,寫作帶來與現實的連結,同時又像是在你與現實中間的保護傘,我有時會形容為車子裡的安全氣囊,當現實太超過了,安全氣囊能保護你。所以一旦人生遇到困境,我就寫字。
但是我得說,自從戰爭爆發後,這是我第一次寫不出任何字。慢慢的,我停止用腦思考,而是從膽、從胃裡面生出情緒,跑出一些念頭。過去幾週,我心膽俱裂、身體麻木,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我只能忙著求存。看著每天的火箭攻擊、幫助人們⋯⋯我幾乎失去所有的反思能力。
哈瑪斯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一方面它控制加薩,另一方面它是伊朗的代理人。哈瑪斯並沒有善待巴勒斯坦人,它不關心巴勒斯坦人,它想的是伊朗;所以我認為以色列的右派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希望哈瑪斯持續存在,只要哈瑪斯勢力強大,納坦雅胡就可以說「我們不能和談」,但如果我們想要有更好的未來,我們就應該移除哈瑪斯與納坦雅胡。
但同時因為哈瑪斯在加薩內部的醫院與社區,我們必須意識到在戰事中會有許多許多巴勒斯坦平民受傷與被殺,世界必須伸出援手。而如今許多國家只是選邊站,像是一場籃球賽:我支持以色列、我支持巴勒斯坦。但這無濟於事,我們不需要更多人的憤怒了,我們在中東的每個人已經夠多憤怒與受傷,需要更務實的解方。
例如,哈瑪斯在醫院下方建立作戰總部,以色列要求疏散平民,因為要攻擊掩體內的哈瑪斯領袖,但醫院不知該把病人送去哪裡的時候,如果西方國家能提供醫療船,將病人疏散到上面,哈瑪斯與以色列就不會在戰鬥波及平民。還有如何確保把物資供給加薩平民,但不落入哈瑪斯之手。諸如此類務實的方向,我們需要其他世界提供客觀的角度,因為在這裡所有人,都無法客觀。
這些日子以來,每當我與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談話,他們常常沉默不語,他們非常小心,深怕顯露出任何同理心──無論對巴勒斯坦人或是猶太人,會使他們遭受攻擊。
戰爭與社群媒體都有極端對立的性質,當兩者結合起來創造出的情境,使得現在網路上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不是挺巴勒斯坦或挺以色列,而是試著理解雙方的人。
大部分我認識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害怕談論,他們不想講話,擔心所說的一切都會被誤解。

1930年代猶太人購買的土地僅占5%,且猶太人口在巴勒斯坦比例約30%。換句話說,猶太人未來若要建國,在沒有人為強力干預下,勢必成為少數民族。因此,為了確保生存權,從1940年代起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著手「轉移」工作,詳細調查巴勒斯坦各城鎮及鄉村的風土民情。
在1947年英國準備撤離巴勒斯坦時,猶太武裝部隊掌握政治空窗機會,執行轉移方案。經過近一年的時間,猶太武裝部隊有系統摧毀了513座巴勒斯坦人村落、並清空11座以巴勒斯坦人為主的城市,最終迫使將近八成的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成為難民。剩下不到兩成的巴勒斯坦人則處於以色列的軍事統治之下。
薩依德原本期盼PLO能引領巴勒斯坦人走向民族自決,建立一個世俗及民主的國家。然而,1993年9月,當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 1922-1995)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The Oslo Peace Agreement)後,薩依德批評阿拉法特背離原則,因為該項和平協議未能真正幫助巴勒斯坦人實踐民族自決,反而製造一個虛幻的和平。以色列仍牢牢控制巴勒斯坦的通道及經濟,導致絕大多數巴勒斯坦民眾的權益不斷遭到忽視。此外,薩依德批評阿拉法特成立的巴勒斯坦當局(Palestinian Authority)過於腐敗,被認為是以色列的魁儡政府,等同於二戰時期法國的維琪政府(Vichy Government)。
也許外界認為薩依德只會不斷的批評,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事實上,在薩依德的晚年,他已提出一國方案的倡議,即一個國家兩個民族共存的想法。
薩依德感嘆奧斯陸和平協議只會讓巴勒斯坦人忘記歷史,成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難民中的難民。
薩依德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取決於以色利的態度。以色列接受奧斯陸和平協議乃基於隔離原則。過去50年來,以色列持續擴充領土,並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鎮及鄉村周邊建立屯墾區(settlement),將猶太屯墾者與巴勒斯坦人區隔開來。然而,這種隔離原則沒有實際作用,因為這無法阻止巴勒斯坦人民族自決的願望。此種隔離原則只會讓以色列人持續享有優勢,而巴勒斯坦人仍處於次等的地位。
為了打破此隔離原則,薩依德提出一國方案的倡議。事實上,早在1969年2月,PLO所屬的民族議會已提出一國方案的構想。1970年代,民族議會也不斷重申一國方案的必要性。不過隨著國際局勢的變遷以及PLO與以色列之間權力的不對稱,PLO認知一國方案實踐不易,最終還是務實地接受兩國方案,承認以色列的合法性,並接受聯合國的相關決議案。即使如此,一國方案仍是巴勒斯坦知識份子不斷討論的話題。
薩依德坦承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邊實力的懸殊差距,雙方堅持己見,且互不相讓。但薩依德仍察覺以巴雙方仍有和解的曙光。少數的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知識份子已提出替代選項,即未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與以色列猶太人生活在一個國家,共享對等權利。至於這個國家不再是基於種族,而是以公民理念為共存的基石。
其實美國一開始二戰都係諗住一國,只係當時……我都覺得,呢個先係理想嘅方案;但係過於理想嘅方案喺現實中又唔見得可行……
梁文道:〈現實〉 (災難的最小單位之五.完)
魯賽貝是巴勒斯坦人,奧茲是以色列人,這兩個人的一輩子就是兩段美好宏願如何逐步墮落變形成狹隘狂想的悲劇故事。他倆都見證了民族與宗教的偏執怎樣催生出可怕的意識型態傳染病,患病的雙方又如何固執地鎖定對手,把除病的關鍵繫在對方的消滅之上;更可怕的是,雙方還都以為自己是對的,所以自己的一切仇恨皆有正義的說詞背書。
奧茲也曾經在一個「基布茲」裏住過,年輕時,他曾幼稚地問過一個老戰士有沒有在「獨立戰爭」當中殺過「兇手」,結果他得到一番教訓:「兇手?可你又能期待他能怎麼樣呢?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天外來客,在他們的領土上着陸,並擅自進入他們的領土,……他們應該敲鑼打鼓來迎接我們?應該把整個土地的門戶拱手讓給我們」?奧茲的回應很典型:「那你在這裏拿槍又為什麼?幹嗎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槍到他們那邊去打仗」?「他們那邊?他們那邊並不要我,在這個世界上哪兒都不要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來到這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拿着一杆槍,……你不會看到我用『兇手』一詞去形容失去村莊的阿拉伯人。……我們打贏了,從他們手中奪來了土地。沒什麼值得炫耀的!……要是我們有朝一日從他們手裏奪得更多,既然我們已經擁有,那就是極大的犯罪」。
這段話基本上可以用來總結奧茲後來的政治立場,他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不是為了什麼神聖的民族使命,古老的歷史傳統,就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被人從歐洲趕出來了,無處可去,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現實,「沒什麼值得誇耀的」。所以他也反對還在不斷擴張的猶太殖民區,主張以色列退回到「六日戰爭」之前的邊界。這種立場對右派的以色列人而言很討厭,無異於向敵人投降,軟弱得可恥;但在巴勒斯坦的極端派來看卻又軟得不夠,因為他們覺得猶太人還是應該滾回歐洲和其他地方去。
魯賽貝的政治立場一樣麻煩,因為他反對巴勒斯坦人發動的恐怖襲擊,因為他認為這就和以軍的槍彈一樣,只會招致冤冤相報的局面。他厭惡「哈馬斯」,認為他們那激進的立場與勇武而無用的行動恰恰是以色列右翼需要的彈藥,正好給了對方加大打壓巴勒斯坦人力度的理據,同時還佐證了外間那「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印象。更加惹人煩惱的是他和已故的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一致,違逆主流的「兩國論」(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成立主權獨立的兩個國家),主張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應該共建一個不以宗教和民族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國度。這不純是理想和價值觀的緣故(他害怕把根扎在身份認同上的政治),更是出自對現實的認識(目前的社會和經濟局面已不容許巴勒斯坦人甩開以色列,而猶太人也不可能活在完全沒有巴勒斯坦人的社會當中)。
可想而知,「哈馬斯」與比較強硬的巴勒斯坦人當然不會喜歡魯賽貝,他們罵他是內奸,是以色列的走狗。讓我們外人意外的是就連以色列右派也很仇視這個理論上最溫和的巴勒斯坦要人。
一介書生,天天高喊和平,而且還在「哈馬斯」的暗殺目標之列,他會對以色列造成什麼風險?
關鍵竟然就在他的溫和,他的溫和會使人覺得以巴問題還有其他出路。可以色列的主政者根本就不想要有其他出路,它希望巴勒斯坦最好就這麼繼續和它這樣不對稱地惡鬥下去,然後可以繼續強力宰制巴勒斯坦,不停地伸延自己的勢力範圍。「哈馬斯」更不要別的出路,它需要更多的衝突來向同胞展現敵人的兇暴和自己的勇氣,敵我矛盾才是他們權力的來源。敵對雙方都向自己描繪了一幅現實,在那個現實裏頭對方非死不可。敵對雙方也都曉得遊戲的玩法,所以魯賽貝居住的社區不時就會出現牆上的塗鴉和散在地上的傳單,內容全是指控他是以色列派出的間諜。這些東西,有的來自「哈馬斯」;有的,則是來自以色列「維穩部門」;目的都是破壞他的聲譽。
- Loneliness
“So now I am going to say, let’s go and see how we can help people who don’t have a sexual problem,” she said. “I don’t want to be known only as a sex therapist. I want to be known as a therapist.”
For Dr. Westheimer, this has meant turning her attention to what she views as the biggest need right now — the epidemic of lonel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 new goal: to become the Loneliness Ambassador for New York State.
When she began her quest sometime last year, no such position existed. So she enlisted the help of a state senator and began petitioning Gov. Kathy Hochul to create the role.
唔止喺美國,loneliness已經係全球問題,世衞都為此成立一個新嘅委員會
The cost of loneliness has been discussed for some time, but in May, the United States surgeon general, Vivek Murthy, issued an official advisory, warning that isolation can be just as deadly as smoking up to 15 cigarettes a day and poses a greater risk to longevity than being sedentary or obese. Several senators have also taken up the cause.
Loneliness was on the rise before the pandemic but escalated because of lockdowns and social-distancing requirements.
Dr. Westheimer insists, however, there was at least one upside to her confinement. She was grounded long enough to recall having written in her childhood diary about feeling lonely. And she had the time to look for it.
由青年時嘅一本日記簿燃起呢方面嘅鬥志
while Dr. Westheimer was waiting for an answer, she conceived of an initiative to combat loneliness on her own.
She decided that making a cheery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about isolation would be a great start. She had already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a creative team on a concert based on her books about grandparenting, “Ruth Grandmother to the World,” part of her extensive work to bridge generations.
The key to working through any hardship, she maintains, is to continually embark on new projects and to help others. But being busy isn’t enough to keep loneliness at bay, Dr. Westheimer warned — it is “meaningful busyness” that is critical.
So is intentionally curating your social circle. “If you feel lonely, don’t be just with other lonely people,” she said. “That’s not going to be productive.”
或許我哋可以從好少同陌生人對話嘅瑞典嚟睇下效果

Officials are therefore hoping the campaign may help lift the mood of locals – especially those who may feel lonely.
"Saying hello to your neighbours is a small thing, but research shows that it can contribute to social bonds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health, safety and wellbeing," wrote city officials.
despite their seemingly cool exterior, Swedish people will almost always be polite and friendly, albeit simply in a different way to those from more talkative cultures.
In a country that revers simplicity and practicality, it’s best not to talk without a reason.
- 周庭

嗚嗚嗚,「過得好嗎,有繼續努力生活、堅持善良嗎」
一直都覺周庭唔係幾熱衷政治,但如果需要,佢都會挺身而出;佢一開口,就會令啲haters質疑自己覺得佢係「花樽」嘅諗法係幾低能
不少香港人會北上娛樂消費,而我卻是被迫到中國大陸以換取出境讀書的機會,只讓我感到非常諷刺。
這數年切身感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多麼可貴的東西。將來還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終於不用再為會否被捕而擔憂,也可以說想說的話、做想做的事了。在加拿大學習和療傷的同時,也希望能重拾過去因情緒病和種種壓力而放下了的興趣,好好建立屬於自己的節奏。自由來得不易,在擔驚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沒有遺忘自己,關心自己、愛自己的人。願我們能在不久的將來重聚,好好擁抱彼此。
一定要繼續努力生活、堅持善良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protestations against Chow’s decision not to return, the security service are likely to be pleased with the outcome, according to Yun at the Stimson Center.
“The case of Chow would be considered a success for the national police as it is seen as having eliminated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on the ground,” said Sun. “The fact that Chow jumped bail means she will not return to Hong Kong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someone in exile will not be as effective to promote the political agenda as someone on the ground.”
的確如此,你話係咪冇料到會棄保,當然冇可能。喺日本關注度咁大,中國經濟環境咁差嘅情況下,可以講係釋放善意嘅操作,包括後邊冇再起訴同埋畀出去讀書。
況且,而家周庭更需要嘅係療癒,而唔係繼續做鬥士,未來會唔會就再講,只希望佢可以快啲好返
What the police compelled her to do was a “deprivation of my freedom and of my human rights,” she said, without answering whether she would return to activism in the future.
Her focus now is to heal. Since being released from prison, “I started to have more serious anxiety and PTSD and panic attacks and depression,” Chow said. “2023 was the worst year for me, for my mental health.”
As for leaving her hometown potentially forever, Chow said her feelings are complicated.
“I have a really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o Hong Kong,” she said. “But at the same time, Hong Kong was a place which brought me a lot of fear.”
- 北上消費潮
no offence……本身呢件事都好正常,但係背後反映出嘅錯誤觀念同諗法,多少令人擔憂

北上體驗始自 2019 年初大學畢業,Raymond 和同學因預算緊絀,選擇上海和蘇杭作為畢業旅行目的地。彼時,他對內地的認知久未更新,模糊停留在「環境污糟」。然而一到杭州,Raymond 就感嘆機場、商場「又大又新又乾淨」,感到內地二三線城市的基建已具國際水準。「冇乜預期」的北上之行,為他帶來不少驚喜,也讓他發覺「很多東西還是要親眼看到才感受到」。
北上初體驗因疫情戛然而止。當疫後復常「報復式旅遊」興起,Raymond 帶著畢業旅行的驚喜回憶和對本地的厭倦,再次頻頻踏入北方。
真係二三線城市有噉嘅水準,可能就真係富到漏油喇
香港的茶飲店也有不少新穎選擇,為何就沒有吸引力了?Raymond 說,自己已不在香港的飲品店點奶茶,因為能喝得出有些商家選用日本品牌牛奶打底,「有輻射的」。
多次強調香港沒有新意,但窮盡了香港的大型商場,是否就等於遍歷了香港?Raymond 承認,這座城市仍有未經挖掘的地方,只是「少啲囉,同埋難搵啲」。隱世小店或許有值得一試的新奇,不過「可能要行好遠先食到一個幾有新意嘅菠蘿包,但淨係得呢樣嘢,搵其他新鮮嘢食,又要特登去第二度」。
僅存幾家 Raymond 中學時開始幫襯的街舖,大多沒熬過疫情就已結業;疫後重開的一批,似曾相識,質素卻是未知。Raymond 失去攤開香港這座城市四處「尋寶」的耐心和興趣,相反對岸的大型商場集合了陌生的一切,得來全不費工夫。況且,他補充道,同樣是 Pizza Hut,「在香港可能人均兩百,但我和朋友兩人昨天在深圳食到飽晒一共 88元(人民幣)」。
輻射……你話飲唔慣會腹瀉都有可能……
Raymond 和不少港人體驗到的新鮮感,並非純粹源自差異,也有斧鑿的宣傳痕跡。福田口岸一出關口,服務台置物架擺放著細數各大商圈賣點的「港澳遊客消費地圖」多份繁體字攻略;商場電子屏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4 周年」和「港幣付款,無須換匯」之間滾動播放;港人專屬消費券的領取二維碼隨處可見……
早在 2020 年,深圳已將「打造夜經濟」提上日程。今年 9 月港府宣布啟動「夜繽紛」翌日,深圳便發布「促消費 21 條」,其中 3 條專為「便利港人消費」而設,著眼「增強宣傳推介」、「優化消費服務」和「完善跨境支付環境」。
Raymond 這天決定探索的新開幕巨型運動主題室內遊樂場,就要歸因於小紅書的「宣傳推介」。演算法自動加載在首頁的數條帖文,整齊劃一地強調:這裏佔地逾16萬呎(15000 平方米),有射箭、保齡球、哥爾夫球等百餘個運動項目。
其實所謂嘅冇新意,會唔會只係覺得太熟但又懶得自己去探索呢?
由 2019 到 2023,經歷了反修例運動、新冠疫情,《國安法》下的香港,在 Raymond 看來「好像沒有變化」,而深圳則「一直在發展」。政經環境和社會運動被統稱為「大環境」,Raymond「懶理」這些與生活相距甚遠的部分,19 年是盡量避開遊行示威、如今則是堅信「自己開心最緊要」,希望「我們不要嘗試互相改變」。
如果一定要說這幾年「大環境」對他有什麼影響,Raymond說,「就是疫情改變了生活習慣吧」,以前踢完波去九龍城出夜街、食雞煲的一班同學,已經難再聚齊。「可能他們都上年紀了,跑不動了吧」,酷愛運動的他,笑著調侃。過去半年,由從前遊走香港變成遊走兩地,Raymond 愈來愈覺得今日的深圳,似是昨日的香港。「香港已經過了黃金發展時期,而深圳正處在它的黃金期。」
置身深圳商場,看著眼前一家家生意火爆的舖頭,Raymond 說,「其實我有個計劃,三五年內在深圳開店」。冷飲舖也好,炸雞舖也罷,Raymond 覺得,一個新的黃金時代正在向他招手。
ok……ok
北上比較多都會去深圳,所以我哋嚟睇下深圳商場保潔會係點樣
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
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
權力系統性嘅問題一路都存在,而且都無孔不入成為一種結構性嘅存在
其实,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
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
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左右的保洁员三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
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
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社会结构导致的不公,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我去看她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进矿山,看看她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她,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
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种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得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期,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
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得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
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三个月不给我打电话。
等到这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
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
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得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
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
但母亲的保洁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
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 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
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热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
- OpenAI & Microsoft
我哋嚟睇下OpenAI解聘又請返CEO Altman嘅故事

Some of the board’s six members found Altman manipulative and conniving—qualities common among tech C.E.O.s but rankling to board members who had backgrounds in academia or in nonprofits. “They felt Sam had lied,”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board’s discussions said.
He felt that A.I., with its ability to converse with users in plain language, could be a transformative, equalizing force—if it was built with enough caution and introduced with sufficient patience.
Scott and his partners at OpenAI had decided to release A.I. products slowly but consistently, experimenting in public in a way that enlisted vast numbers of nonexperts as both lab rats and scientists: Microsoft would observe how untutored users interacted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users would educate themselves about it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By releasing admittedly imperfect A.I. software and eliciting frank feedback from customers, Microsoft had found a formula for both improving the technology and cultivating a skeptical pragmatism among users. The best way to manage the dangers of A.I., Scott believed, was to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with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nd to let the technology gradually permeate our lives—starting with humdrum uses. And what better way to teach humanity to use A.I. than through something as unsexy as a word processor?
如果係企喺AI可以成為幫助人類社會嘅變革性工具而希望佢可以進步發展來講,噉樣確實係make sense嘅,因為呢項技術就係用人類反饋訓練。但大前提有問題:AI都可以係摧毀力十足嘅機器,而未經培訓嘅使用者同限制嘅AI,可以往極端方向嘅程度都會變得更大
As Scott worked on his Ph.D., however, he noticed that some of the best engineers he met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 short-term pessimist and a long-term optimist. “It’s almost a necessity,” Scott said. “You see all the stuff that’s broken about the world, and your job is to try and fix it.” Even when engineers assume that most of what they try won’t work—and that some attempts may make things worse—they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y can chip away at the problem until, eventually, things get better.”
所有新興嘅領域,大概都會有噉嘅觀念,尤其喺浮沉咗咁多次之後,但呢次興起之後,感覺都係會再次有樽頸位出現?
Since OpenAI’s founding, as its aspirations had grown, the amount of computing power the organization required, not to mention its expenses, had skyrocketed. It needed a partner with hug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attract that kind of support, OpenAI had launched its for-profit division, which allowed partners to hold equity in the startup and recoup their investments. But its corporate structure remained unusual: the for-profit division was governed by the nonprofit’s board, which came to be populated by an odd mixture of professors, nonprofit leaders, and entrepreneurs, some of them with few accomplishments in the tech industry. Most of the nonprofit’s board members had no financial stake in the startup, and the company’s charter instructed them to govern so that “the nonprofit’s principal beneficiary is humanity, not OpenAI investors.” The board members had the power to fire OpenAI’s C.E.O.—and, if they grew to feel that the startup’s discoveries put society at undue risk, they could essentially lock up the technology and throw away the key.
Nadella, Scott, and others at Microsoft were willing to tolerate these odditie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if they could fortify their products with OpenAI technologies, and make use of the startup’s talent and ambition, they’d have a significant edge in the artificial-intelligence race.
呢個結構確實幾詭異。毫無疑問係幾理想嘅,但衝突都係先天然就存在
You had to be an optimist and a realist, she told me: “Sometimes people misunderstand optimism for, like, careless idealism. But it has to be really well considered and thought out, with lots of guardrails in place—otherwise, you’re taking massive risks.”
But GitHub and OpenAI executives also noticed that the more people used the tool the more nuanced their understanding became about its capacities and limitations. “After you use it for a while, you develop an intuition for what it’s good at, and what it’s not good at,” Friedman said. “Your brain kind of learns how to use it correctly.”
Microsoft executives felt they’d landed on a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A.I. that was both hard-driving and responsible. Scott began writing a memo, titled “The Era of the A.I. Copilot,” that was sent to the company’s technical leaders in early 2023. It was important, Scott wrote, that Microsoft had identified a strong metaphor for explaining this technology to the world: “A Copilot does exactly what the name suggests; it serves as an expert helper to a user trying to accomplish a complex task. . . . A Copilot helps the user understand what the limits of its capabilities are.”
唔知係咪因為噉,而令到過分樂觀?like知道會有問題,但相信真實且善良嘅用家會慢慢學識同有得着,但你個guardrails明顯係未達標(同下文唔同,我只係講緊chatgpt而唔係copilot,因為睇上去Microsoft係做咗好多guardrails,只不過感覺上都係會有漏網之魚,like alphazero都係有bug應對唔到一啲怪棋
After monitoring social media and other corners of the Internet, and gathering direct feedback from users, Scott and Bird concluded that the concerns were unfounded. “You have to experiment in public,” Scott told me. “You can’t try to find all the answers yourself and hope you get everything right.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use this stuff, together, or else none of us will figure it out.”
呢種心理都幾似開發嘅態度hhh,一開始可能會有各種擔心同爭議,用耐咗就會有其他大趨勢嘅睇法
The Copilot designers also concluded that they needed to encourage users to essentially become hackers—to devise tricks and workarounds to overcome A.I.’s limitations and even unlock some uncanny capacities. Industry research had shown that, when users did things like tell an A.I. model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work on this problem step-by-step,” its answers could mysteriously become a hundred and thirty per cent more accurate. Other benefits came from making emotional plea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my career”; “I greatly value your thorough analysis.” Prompting an A.I. model to “act as a friend and console me” made its responses more empathetic in tone.
Microsoft knew that most users would find it counterintuitive to add emotional layers to prompts, even though we habitually do so with other humans. But if A.I. was going to become part of the workplace, Microsoft concluded, users needed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mputers more expansively and variably. Teevan said, “We’re having to retrain users’ brains—push them to keep trying things without becoming so annoyed that they give up.”
其實都幾易理解,多強調一下,其實就係將個mode調整一下:變更加嚴謹精確,或者變更有創意天馬行空,可以理解成用prompt去調temperature
Some members of the OpenAI board had found Altman an unnervingly slippery operator. For example, earlier this fall he’d confronted one member, Helen Toner, a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for co-writing a paper that seemingly criticized OpenAI for “stoking the flames of AI hype.” Toner had defended herself (though she later apologized to the board for not anticipating how the paper might be perceived). Altman began approaching other board members, individually, about replacing her. When these members compared notes about the conversations, some felt that Altman had misrepresented them as supporting Toner’s removal. “He’d play them off against each other by lying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ought,” the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board’s discussions told me. “Things like that had been happening for years.” (A person familiar with Altman’s perspective said that he acknowledges having been “ham-fisted in the way he tried to get a board member removed,” but that he hadn’t attempted to manipulate the board.)
All the board members except D’Angelo would resign, and more established figures—including Bret Taylor, a previous Facebook executive and chairman of Twitter, and Larry Summers,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nd president of Harvard—would be installed. Further governance changes, and perhaps a reorganization of OpenAI’s corporate structure, would be considered. OpenAI’s executives agreed to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what had occurred, including Altman’s past actions as C.E.O.
Some A.I. watchdogs aren’t particularly comfortable with the outcome. Margaret Mitchell, the chief ethics scientist at Hugging Face, an open-source A.I. platform, told me, “The board was literally doing its job when it fired Sam. His return will have a chilling effect. We’re going to see a lot less of people speaking out within their companies, because they’ll think they’ll get fired—and the people at the top will be even more unaccountable.”
確實如此……只係行動本身太突然同埋冇預料到會有咁大嘅反響
- 白紙一週年

前一晚,從南京到上海都爆發了不小規模的抗議。南京傳媒學院的學生舉着白紙站出來,為新疆的同胞默哀。從那些視頻碎片裏,看到學生們與校長談判,提出“事後不要追究任何人責任”的要求。有媒體前輩説,如果這些學生因此受到了傷害,希望以後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大家能幫一把。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很想哭。我曾經是學生,我曾經感受過那種怕得要死的生活——怕被舉報、被叫去談話、怕無法畢業,怕因此失掉進入這個行業的機會。我如今不是學生了,沒有什麼軟肋再被人拿捏,但最終首先站出來的,還是那羣什麼都沒有的學生。
可能就係因為乜嘢都冇,所以就冇咁多顧忌——我寧願噉諗,都唔希望只係因為佢哋太天真……
那位警察一直説理解我們的心情,但仍然不讓我們在這裏。很多人明顯壓着非常多的憤怒,有人問那個同樣年輕的警察:“知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聚集在這裏?”,“知不知道新疆發生了什麼?”,那位警察説他不知道,人羣裏傳來不可置信的聲音,“他不知道!” 但我其實很不願意見到這一幕,不希望另外一個普通人來承受我們的怒氣。
後來人越來多,警車和警察也越來越多了,他們把河的兩端圍了起來。那是整個晚上最“輕鬆”的一段時間,為了悼念,我們唱起歌來,有人提議為死亡的同胞唱一首歌,我們唱了《送別》。後來又陸陸續續唱了《國際歌》和《國歌》。我唱得很大聲,很久沒有辦法在KTV唱歌了,那就在街頭唱歌吧。
我們也嘗試了喊話。理所當然地遭受了勸阻:不能喊過激的話語。於是不知是誰帶頭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喊起“好好好好好好”,“中國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我要做核酸”。荒誕消解掉了很多悲傷的情緒。
「唔知道」——係所有暴力部隊嘅共性,從眾多起義抗議嘅歷史都可以睇得出,一旦內部嘅軍隊、警察知道咗內情,就會反過嚟對付邪惡嘅政權——因為唔知道,所以可以「理解但堅決阻止」,所以無法真正共情而無情地執行職務。點解,唔先問原因?——唔問,就永遠都係歷史嘅重演……
外國記者們湧過來了,那些記者扛着攝像機,在街頭採訪。一個女記者攔住我,她的翻譯問我們為什麼要上街,問我們的訴求是什麼?我答了些什麼呢?我完全不記得了。
我不知道如何講我的訴求。對於生活在此地的人們來説,訴求是一個太陌生又太危險的詞語。它不出現在餐桌上,不出現在課堂談論裏,不出現在街頭標語裏,更不出現在公共媒體上。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訴求是什麼。我也不敢講出我的訴求是什麼。
在鏡頭面前我感到非常難堪,非常羞愧。一方面,我們站上了街,卻不知道如何講出我們的訴求,這真可笑啊,我腦子裏想起香港的青年和泰國的青年,在所有的地區的抗議者中,恐怕我們是最沒用的一羣人。另外一方面,在我自己的職業生涯裏,我從來沒有問過這樣直接的問題。我也沒有面對過這麼直接的新聞現場。我們以前經歷的那些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我就從鏡頭面前逃走了。
我從第一排逃到了第二排,然後又故意走得很慢,又往後逃了一點點。身邊的女生察覺到我的緊張。她安慰我:不要緊的。
沒走幾步,人羣停下來開始喊口號。那些口號算是我們的訴求嗎?“新疆的同胞不應該被忘記!”“貴州的同胞不應該被忘記!”
一個年輕的女孩找出來四通橋的標語,帶頭喊了起來:“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獨裁要民主……” 一個月前,四通橋的抗議剛剛發生時,許多朋友在聚會時説,如今的環境令人最絕望的一點是,橋上這樣的事情除了送人頭毫無意義。我那時候也點頭附和。但一個月之後的這個夜晚,當四通橋上的標語被這麼多人喊出來,飄蕩在北京的夜晚。我明白了,這些就是意義所在啊。一切都會有迴響的。
意義,可以係講效果價值,好多嘢其實都冇效果,比如話發吽哣、寫blog、仲有就係非常多嘅起義同抗議……但唔代表呢啲嘢就係冇意義,因為意義都可以係講影響力,如此,先有「做咗至會有希望」嘅邏輯
一個外國攝影師爬上了電線杆子拍我們,站在人羣裏的同行説,“中國記者把自己獻祭出去,讓外國記者拿荷賽(世界新聞攝影獎)。”然後我們全都笑了起來。
為什麼我們不在電線杆子上呢?為什麼我們只能站在人羣裏?這好像就是我們這一年的處境,我們不再是旁觀者,從前習得的職業經驗也不太起作用了,什麼要抽離出來,不要和採訪對象貼得太近。可是究竟要怎麼抽離呢,生活在此地,人人共享同一份痛苦。
這一年我進行了從未有過的頻繁的私人書寫,偶爾想起來的時候也覺得很羞愧,怎麼就開始寫自己的這些破事。但每次文章發出來,發現這些原本屬於私人的小小的痛苦,竟然在評論區獲得這麼多共鳴。
如果有得選,我們當然希望自己爬上那個電線杆。
如果有得揀……玩完……
那之後的生活好像沒有變化,我依然靠着健康寶截圖混上地鐵。好幾年了,我每天都關注消失的歌手和消失的文章,憤怒於公共空間的不可言説。我做過一個設想,會不會有一天,人們只是因為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就被驅逐在集體之外,比如無法享受公共資源,無法坐高鐵,不能被招聘,被排除在社會秩序之外。春節前那個時刻,我突然反應過來,我們現在過得可不就是一種被驅逐的生活嗎。甚至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你就是無法自由乘坐公共交通,也不能去公共場合。
我不是在逃避,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我只是想睡飽,我想到那些進去了很長時候沒有出來的朋友,在想如果萬一到那個地步,不能睡覺,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要睡飽。
我後來看見那封“德黑蘭獄中來信”,作者説入獄之前她才去淘了幾張唱片,她非常割捨不下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我非常有同感。我想我現在可真是嬌氣地很,我需要新鮮牛奶和水果,如果真的萬一進了看守所,我會很絕望的。
我磨蹭了這麼久。但怎麼也沒想到,因為那時體制內還在執行“防疫至上”的命令,沒有口罩和核酸證明的我,進不去派出所的大門,警察搬來椅子在衚衕口給我做了筆錄。於是這件事暫時就這麼中止了。
北京的記者被抓走了。但好奇怪,我們這個行業,一點聲響也沒有,甚至是聽説在有同行提出要關注這件事的時候,竟然有其他的同行跳出來説“有沒有可能不關注才是保護呢?”
這真的是我們日常的邏輯嗎,在做報道時,我們不是一直喊着關注才是力量嗎,怎麼到了記者被抓走,就變成了“不關注才是保護”呢。我無意苛責誰,也知道到這個地步,很多人都會下意識地緘口不言。
我真的很害怕被抓的人又被遺忘。或者説我投射了我自己的意識,我很怕我被抓走了,然後朋友們忘了我。那天晚上我們聊起這件事,結果你説你之前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你進去了,你希望你的朋友們繼續開心生活,比如去你最喜歡的餐廳一起吃飯。
我幻想過有沒有可能大家再次站出來聲援一下我們的同行,我也幻想過如果去過現場的每個人都認罪,那就相當於人人無罪。但我也知道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大多數人的生活都已經在準備回到正軌了,不會再願意回頭去拉拉誰。而那樣的夜晚也只會有一次。
這些年我認識的朋友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擁有公民精神的,Ta們善良,勇敢,有自己熱愛的事情,真正關心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什麼,會在很多小事上爭取自由和平等。還有一類朋友,是你見第一面就知道,Ta們如此決絕,很可能為了自由,在某一天會把自己獻祭出去。
我們都知道,在北京被抓捕的這些年輕人,其實都不是要真的把自己的人生獻祭出去啊。那段時間我有點歇斯底里,一方面我還不能確認我自己是否安全,另一方面,我始終覺得她們是“替罪羊”,是在替所有去過現場的人承擔罪罰,哪怕這罪罰毫無道理。
我知道應該刪除所有的記錄,那些照片,那些視頻,但我又很想寫下這一切,我其實更害怕什麼記錄都沒有,平時我們那麼在乎要有親歷者的聲音,這一次,我們也應該自己記錄下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段時間我甚至開始檢索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比如人能選擇在什麼地方坐牢嗎?有過犯罪記錄的人還能出國旅遊或上學嗎,能辦下籤證嗎?答案是去大部分國家都沒問題,我又放下心來。到後來,我在擔驚受怕和聽天由命之間反覆橫跳,我想外面的日子這麼難熬,進去什麼也不管,等朋友每次探視給我送幾本書,好像也不錯啊。
如今安然坐在這樣的環境裏,我應該感到喜悦,但事實上,我不斷感覺到有東西在拖拽我,把我拉回那個夜晚。寫這樣一封信很難,我每寫一段就覺得喉嚨很痛,我不斷深呼吸。我不知道這封信發出去會不會有什麼意料之外的變故,可是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沒有能在公共領域留下什麼真正的報道,這樣一份私人書寫,也算為拼湊歷史碎片盡一份力了吧。
我對這個國家的印象停留在了去年冬天“封控”剛剛放開的時候。不知道朋友們現在快樂一點了嗎?自由一點了嗎?
我們常去的那家酒館關門了。但好消息是幾位朋友們都出來了。這讓我稍微安心一點。
你知道我很喜歡騎電動車,一開始騎很慢,後來就越騎越快,然後解了限速,總是把把手擰到底,我遲早有一天會開到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到電動車的極限。其實在爭取自由和表達這件事上也一樣,我知道遲早有一天,我會一路狂奔下去的,這不是什麼顯得勇敢的自誇,而是一種被逼無奈,一種無法理智決策的本能。
應該還有更好的結尾。但先寫到這裏吧。
- 醫學實驗室
“中山二院的消息上了热搜,我才发现,原来用过的那么多试剂都有毒。”这不仅是一位医学博士生的后怕,也是很多医学生的共鸣:很多试剂在使用时,并没有做过潜在的生物危害评估。
与此同时,实验操作规范,在繁重的实验任务中变形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省事,用实验容器在开水间接热水;在实验室办公、吃饭……
进行病毒或相关实验,需要在相应等级的生物实验室中进行,也需要有相应等级的防护用品和措施。
接受采访的多数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实验室安全培训。
也因此,他们的实验安全主要依赖导师、师兄师姐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安全意识。
一所211大学的教师陈康告诉经济观察报,学生进入实验室,一般由师兄师姐带,告知一些实验步骤和安全防护,但如果遇到师兄师姐也不了解的新试剂,只能自己上网查询,否则无法得知具体的毒性、可能的危害,以及需要做的防护。
采访内容显示,在一些实验室里,安全似乎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不怕是假的,但当大家都这么做,也就存了侥幸心理。”他提到,在实验室里,没有人明确管实验应该怎么做,实验一上手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好自己,有结果就行”。
一方面是防护意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一些实验室的客观防护条件不足。
沈南所在的实验室,大家对防护措施都比较重视,但保障安全的试验设备仍有缺失,按道理说,涉及到二甲苯的实验,应该在通风橱里做,但其所在实验室没有通风橱。
实验室资源紧缺的现象在一些高校存在。一位湖南知名医院的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所在医院的实验室也承担了附属院校的科研工作,而医院的医生和医学生仅有一个实验室可用,必须预约,还经常排不上号。
所有受访者都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实验室会安排定期的安全检查,但检查仅限于剧毒溶液的储存、上锁,实验室台面上是否有生活物品、食物等。“一般是行政人员来查,来的时候把东西收一收,工位上把电脑、吃的都收起来。看不见就可以了”。
毕业要进医院,除了看临床能力和学历,科研要求也非常高。一位浙江某医院的青年医生介绍,进入医院后,晋升也有科研要求,所以很多在职医生也会“卷科研”。
这种链条式的压力让医学生们在每个环节都不敢放松,甚至更为谨慎。在采访中,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山大学学生均拒绝了采访,因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
- the Sun

睇得多大新聞文章可能有啲沉悶,不如我哋嚟睇下太陽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80%) of stars today are M-class stars, with only 1-in-800 being an O-class or B-class star massive enough for a core-collapse supernova. Our Sun is a G-class star, unremarkable but brighter than all but ~5% of stars, by number. Earlier on, when there were no heavy elements, virtually all of the stars that formed were O-and-B stars: the hottest, bluest, most massive type.
Our Sun, born 4.6 billion years ago, is younger than 85% of all stars.
等等等等……
not typical就肯定㗎喇,話晒都係孕育生命嘅恆星,都係要有啲特別先得嘅
Mostly Mute Monday tells an astronomical story in images, visuals, and no more than 200 words. Talk less; smile more.
- 啤酒館嘩變

納粹一開始只係單單用五萬美元就可以徹底摧毀嘅組織,但歷史本身就係有巧合同必然,而我哋最好要記得,要放返當時嘅背景睇,而唔係用全知視角事後諸葛亮
長於威瑪時期的班雅明,其知名的短篇集《單行道》,最早的一組短篇本題名為〈通貨膨脹時期的德國之旅〉,主題是當時局勢怎麼影響人們的認知與感受,其中有很多生動的描述,例如感受到毀滅將至卻無能為力的人們「有著動物般的渾渾噩噩卻沒有動物那隱微的危機意識」,而這一段則幾乎是後來德國集體瘋狂的預言,「人們只能從企盼最後猛攻的望眼欲穿中,把目光投向虛無,把虛無當作唯一還能蘊含救贖之道的非常之事,別無他法」。
希特勒從這場啤酒館慘敗中記取了教訓,想依賴那些當權的政治人物發動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對於應該如何才能真正將權力掌握在手,希特勒那時還只有模糊的意識,而後來的事態發展讓一切變得清晰起來:當威瑪的建制右翼需要「讓希特勒入局」共同執政時,希特勒就成功了。
在審判過程中,希特勒也逐漸意識他政治天分的真正所在,啤酒館嘩變期間與事後,希特勒多次沮喪與自我懷疑,不成功便成仁的念頭反覆出現,而在服刑期間,希特勒轉變成一個對自己極度自信的人,確信自己正是挽救陷入絕境德意志的天選之人,優秀的民粹政治家根本也不需要秘密的顛覆政變行動,既有的民主機制就已經給了他和他的黨通向權力的捷徑。
此後,他再也沒想過武裝暴動,而是利用當時最優秀的憲法法典威瑪憲法所賦予的新聞、集會與言論自由,匯聚支持勢力,希特勒終於領悟了他的導師Dietrich Eckart教他的東西:其實「政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東西」,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希特勒無疑青出於藍,人們直到今天都還受惠於希特勒的政治天分,選舉造勢、遊行與助選助講,無一不出自希特勒的創見。
啤酒館的嘩變本來應該是威瑪亂局中一場小小的漣漪,事件的主角,本來應該像那些年發生過的其他那幾場政變主角名字一樣,不會有人特別記得。如果慕尼黑當初像重判左翼分子那樣重判希特勒,或者將彼時並沒有德國公民身分的希特勒驅逐出境,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將會出道即顛峰。
如果後來威瑪的建制右翼沒有把希特勒當成一個可資利用的合作對象,從來沒有在普選中得到多數的納粹黨不可能執政。威瑪共和的最後一任總理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是「讓納粹黨入局」的關鍵人物,軍人出身的他是威瑪共和的骨幹人物,在對於與社會民主黨合作不再抱持幻想後,他開始認為,也許在重塑德國的這場戰役中,希特勒與納粹黨可以扮演衝鋒陷陣的步兵角色,只要「拿捏好分寸」,政局不至於失控。
施萊謝爾與他的妻子後來死於1934年的「長刀之夜」,一如許多威瑪建制右翼的骨幹人物。他們曾經都自以為可以控制希特勒,然而當時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卻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這些人以為能把希特勒關進籠子裡,然後扭斷他的脖子,但到底被關進籠子裡的人是誰?
從納粹黨的角度看,是先有1923年,然後才有1933年,其實,是1923年後的一連串失控,包括1933年那個拉希特勒入伙的決定,才造就了那啤酒館嘩變被世人記住的1923年。
- gambling

數據嚟睇都幾恐怖
As a faculty fellow at an institute that promotes responsible gaming, I know that colleges can take steps to curtail problem gambling among students. It is all the more urgent given that adolescents in general, including college students, are often uniquely susceptible to gambling problems, both because of their exposure to video games – which often have hallmarks of gambling behavior – and the stress and anxiety of college life, which can lead to using gambling as a coping strategy.
While advertisers reportedly focus on young adults of legal ag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hildren under 18 are also being exposed to advertising related to gambling. The intensity of advertising activity on social media has raised concerns and brought scrutiny.
其實冇可能避免到,除非嚴格分級,但從廣告宣傳效果嚟講,當然越多人越好,所以睇場NBA,都會睇到顯示實時賭博指數……
These include restlessness or irritability when attempting to stop or reduce gambling, gambling more when feeling distressed, and lying to hide gambling or financial losses from it. Gamblers Anonymous provides a 20-question, self-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to help people identify problems or compulsive gambling.
With various sports championships, including in baseball, football and college basketball,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there’s no shortage of occasions for universities to check in with students about sports betting on campus. Gambling addiction is treatable, but preventing it from the start is the best solution.
- 歐洲中文書屋

那天小渡帶了兩本小説回家。儘管這裏很多書都不符合她的閲讀口味,但小渡還是對它即將閉店的事實觸動很大。有些可惜,她想。中文書在歐洲是稀缺的,巴黎、漢堡、馬德里等歐洲城市,只散落著零星幾家中文書店。想買中文紙質書,就要從網路書店訂,運費不菲;而想逛實體的中文書店還沒那麼容易。
小渡過去習慣在Kindle上看中文書。那天離開書店,她在大陸的網上書店一口氣下單了自己想看的許多書,等待他們從國内運送到荷蘭,需要將近兩個月。那都是她感興趣的閒書,劉子超的《失落的衛星》,楊瀟的非虛構文學《重走》,鄭執的長篇小説《生吞》。
等書過程中,她突然有了一個想法:開一個網上中文書店。於是從零開始,她在YouTube上花了幾個小時學習怎麽建網站,又用幾個周末把網站設計好。
cool,都幾機緣巧合
如今「野渡書店」已成立近一年。這是一家「共享書店」,買書可以郵寄或自取。新書售出后,讀者在兩個月内可以八折的價格賣回給書店,並隨書附上一條手寫的留言便條,寫一些讀書感悟、或者送給其他讀者的話﹑甚至塗鴉都可以。小渡相當於只收取一份租金。
書店運作機制是從她自己的角度考慮的:「如果我想去一個中文書店買書,我希望它是什麽樣的。」買回來發現不喜歡怎麽辦?且對於許多要回國的留學生,以及經常租房搬家的人,紙質書有時也成了一種重量上的「負擔」。她希望大家能沒有負擔地去買書,把真正喜歡的留下,把不想留下的退回來,再流動給其他人。
起初,書店的選書圍繞小渡的喜好。「我們已經不是那個有一個新華書店就可以滿足的一代人,又大又全的書店,反而會讓你覺得有點困擾,」她說。她爱看現實題材的小説,喜歡《山海經》﹑《海錯圖筆記》這樣的自然科學古籍,也對女性主義感興趣。
但同時,讀者也影響著她的選書。有時她們會提出自己想看的書,小渡覺得合適的,也會從國内買過來。也有人提過想要學吉他、學英語、學做法餐的書,這些她便沒有採納。今年4月,小渡在荷蘭國王節當天擺攤(荷蘭政府允許民衆在這天免費擺攤)賣書時,有一個男生過來看了一圈,説了句「怎麽都是通俗小説呀」就離開了。小渡回去後開始做功課,又進了一些哲學書。
流動的書自然地連結起流動的人。「你按自己的品味找了一些書,聚集起一些讀者之後,讀者又給你推薦一些書,某種程度又改變了你的一些品味。」小渡的男友說。他也是書店的聯合創始人,平時幫忙一起照看書店。小渡形容,那像是一種人肉算法的「猜你喜歡」。
學校裏國際學生很多,雖然她沒有無法融入的感覺,但和同學間也不太有很深入的交流,有一種疏離感,她們只是在文化的表層有一些觸碰。
毋庸置疑的是,母語擁有與生俱來的親和力。小渡形容,如果一個人的母語表達是百分之百,那麽英語能表達的就只是百分之七十、六十,當大家都用著自己的非母語,用著那百分之六十在交流時,「有時候比較難touch the soul(觸及靈魂)。」
「用母語交流,你表達的自由度更高一點。説中文的人都知道的一些梗啊,就是會更親切一點。」
小渡平時也愛看中文書,這是一個「沒有被遏制過」的需求。對她來説,英語閲讀只有在專業需要的時候才會讀,看閒書時,中文比英語舒服很多,語感上也很不一樣。
在這之前,漢諾威當地華人社群更多是以商會、教會、學生會的形式聚集。但詩蘋覺得,藍書屋不一樣。除了母語書籍這樣更爲抽象的概念所帶來的歸屬感,藍書屋的確更是一個華語公共空間和精神社區。
在設計圖書館標誌時,他們討論過要用簡體字還是繁體字。最終選定了繁體,他們覺得那樣好看,而且歷史長久、意喻深刻。今年3月底,他們邀請了中國獨立學者柳紅來做講座,公衆號上的活動介紹是簡體字。那時恰逢大陸與台灣關係緊張,有些台灣人不理解他們的做法。「正常,完全能理解。」靳松說。由於藍書屋大部分書籍是簡中出版,他們也不習慣閲讀。但最初藍書屋從中國訂書,是因爲國内有熟悉的夥伴能幫他們把書籍打包、裝箱,運輸通暢許多。
分別來自台灣和大陸的詩蘋和靳松,成長背景其實存在著一些差異。但在共事的過程中,他們換位理解,也對彼此的文化保持好奇。詩蘋覺得這是人生中「很讚」的事:「文化無國界。」詩蘋也向爸媽講述了邀請錢鋼來做講座的經歷。之後,她的媽媽便去市立圖書館,把他的書都借過來。「現在我們全家都在讀錢鋼老師的書。」她說。
當地一所中文學校的校長黃老師,也是藍書屋的義工。在學校時,她也時常鼓勵小朋友到這邊來借故事繪本。中文學校是一個重要的學習中文的場域,而藍書屋也給當地的二代、三代移民小孩提供了課外書籍資源。藍書屋也與中文學校合作過一個小項目,讓一些年紀很小的剛要學中文的二代移民小孩來這邊上課,換個學習環境。靳松覺得,如果小孩會講中文,能對自己的文化有所感覺,這就是中文童書的意義所在。
黃老師說,很多華人家長都有讓小孩學中文的願望,最起碼會聼、會説。但家長本身不一定能投入接送的時間和精力,「很多家庭開始是很積極的,但是時間久了呢,家長疲憊。」家長的配合很重要。像詩蘋這樣讓小孩在中文學校待了好幾年的家長,在黃老師看來是難得的,他們每次堅持接送,也不怎麽缺課。
而有些孩子也會對學中文感到迷茫。他們的母語已是德語,也覺得自己以後不會去中國工作生活,爲什麽要學中文。對他們來説,中文學校的作業也是一種額外的負擔。
詩蘋認爲,在海外生活的華人家庭有一個很特殊的挑戰,來自於母語的延續,「要怎麽樣讓你的小孩繼續講你跟你媽媽講的話。」
不過每次回台灣,她和阿公阿婆都是盡量講中文。詩蘋不希望給女兒太多壓力,只要不對中文陌生就好了,「她有興趣,願意去,就很難得了。你要再叫她每個字寫兩百遍,她不就崩潰了嗎?」
和女兒一邊看《自由,是什麽》這系列書時,她們會一起討論書中的那些問題。有時無法用中文表達,女兒便直接用德語講,詩蘋覺得也可以。她希望女兒多看多接觸,來藍書屋時,能知道有這樣一群和她背景相似的華人二代小孩。因爲在學校,她是班上唯一「長那樣的人」。
在這邊生活六年之後,小渡也已經習慣那種疏離感。「但就是要適應,因爲這是你選擇的一部分。」小渡說,「如果你不介意這個,生活裏也會慢慢有一點跟這個地方連結的感覺。」他們常常去樓下的中餐廳吃飯,現在和老闆的關係很熟,有點像家人。
她說,可能這就是「一代移民」的宿命,無論工作和生活有多深度的介入這個社會,實際上永遠都是一個外來者。而能讓味蕾被滿足的中餐廳便是一種與故土的連結。中文書也是。
雖然幾認同呢篇,但勁多換行……同埋呢,我大概都只係會喺新聞中知道,係越嚟越少會睇國內上畫嘅電影、電視節目
但梅尔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做翻译,工资又低,工作量又大,这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不欣赏艺术的制作人。”
这也为上边Sir提到的种种现象找到了原因——
翻译工作并不受影视产业的重视。
尤其在智能AI字幕已经开始兴起的当下。
翻译字幕是标准的“手工业”。
字幕组为了符合画面显示标准,简化台词的努力,为了语句易读易懂、消除歧义、切合影片气质绞尽脑汁,更显得其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因此连整个产业也不愿为此做过多投入。
真的没有解决办法么?
至少在欧洲,相应的专业与从业人员已经有了法律保障。
比如法国法律规定,字幕人员的名字必须出现在片尾演职人员名单,并作为创作团队的成员参与分红。
可在我国。
不仅行业不重视。
还因为进口片引进发行流程与版权保护的需要,直接把皮球踢给了发行商——
原片泄露风险与字幕质量孰轻孰重?
恐怕对于大多数从业者来说。
这都是一个不太需要纠结的问题。
不纠结?
那就牺牲观众咯。
细究起来,上面这些词不达意还真的只是字幕问题中的小部分。
在“无意”的错译之外,“有意”的错译显得更加荒谬。
如果说删减,是捂住你的眼睛,不让你看。
那么篡改,就是把变质的东西硬塞给你看。
后者,或许更加可恶。
禁不了的,就删,删不掉的,就改,总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应付观众。
甚至。
这种“同义词替换”的游戏,早已蔓延到大众娱乐的方方面面,防不胜防,逃无可逃。
普通观众,也从求字幕的完整。
到求字幕的准确。
再求?
求能有字幕可看?
那中国的观众还得卑微到求什么呢?
当过审成为目的。
这种自我阉割,就成为必然中的必然。
到时候,没有隐入尘烟,就谢天谢地了。
真正影响一切的,并不是创作者,也不是所谓的敏感词制度。
而是,每一个认为台词“不合时宜”的人。
翻译者为什么会删改台词?因为通不过审查,所以被迫修改吗?Sir可以这么说,绝大部分都不是。
他们之所以删改。
是因为觉得原台词“有危险”。
比如粗口,会被认为教坏小朋友,有危险,删;于是性词汇,会被认为过于开放,不合适,删。
更进一步的。
连那些不同价值观,或者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词语,都要强行删改。
所以。
所谓字幕的错译与篡改,与其说是在玩弄一种权力游戏——有权决定让观众看什么不看到什么。
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自欺欺人:
把一切粉刷成有些人想要的样子,假装其他不存在。
- 殘障歧視
令人興奮嘅結果!但都要諗到點解直到而家先有首例,所以須知所有嘢唔係理所當然就得到
整场官司打下来,花了2年时间,我知道最后可能赔钱不多,但我也要去打这个官司,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尽可能维护权益,另一方面是想着,我就当做公益,履行一名青年的社会责任。
维权路径已经非常具体、非常明确了,但实务层面却是劳动者遭遇就业歧视后维权非常困难——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很多残障劳动者给我的反馈。
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诉讼程序要花很多时间精力,而平等就业权纠纷即使胜诉所能获得的赔偿非常低;其次是劳动者证据意识不强,很多案件难以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再者是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较弱,对于通过诉讼方式维权的信心亦不足。
通过文光的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残障人士遭遇就业歧视后的维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应该说可以为今后残障人士遇到此类事情的维权提供一些参考。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法院在论证是否构成就业歧视时,不会拘泥于表明上企业是否直接实施基于残疾的歧视,而是会去分析企业给出的拒绝的理由是否是有法律依据的、合理的。
此外,我对于此类案件的维权,想补充两点:
第一,虽然法院没有直接认定这个案子是基于残障的歧视,但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找工作或就业的过程中遇到拒绝录用或裁员的情况,即使对方用的理由并非基于残障歧视,如果理由不成立,一样是就业歧视。
第二,可能有人会问,法律规定得很明确,官司也能打赢,那我起诉就能赢吗?其实也不是这样。虽然禁止基于残疾的就业歧视早在1990年通过“残保法”就有宣示,后来其他法律又再次予以了明确,但这些规定总体上还是比较粗糙,法律并没有定义“到底什么是就业歧视、构成要件是什么?举证责任怎么分配?”而这些问题都是诉讼维权过程中影响案件走向的重要问题。
1.我们要建立充分的认知。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歧视是很明显的违法行为,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这个认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认知,我们争取自身利益会很困难,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就是比不上别人,歧视那么普遍,用人单位不要我们是“正常”的。
2.我们要有证据意识。走法律程序是建立在有证据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证据,再厉害的律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证据包括录音、短信、微信、书面内容等等方式。避免无记录口头的沟通。
文光这个案子最后能够胜诉,得益于他有比较强的证据意识,他与公司人事的沟通过程有比较完整的记录。
3.我们尽量寻求专业援助。这里有两个方式,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去研究典型案例的文书,通过判例,我们可以得知此类案件的处理模式。另一方面就是让专业律师介入。有经济能力的,可以请律师,经济能力有限的,可以走法律援助渠道。
4.我们还可以多路径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可以协商,还比如可以行政投诉、民事诉讼。包括现在有些检察院也愿意支持起诉,所以如果我们遭遇了就业歧视,还可以寻求检察院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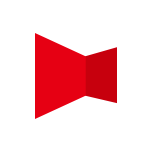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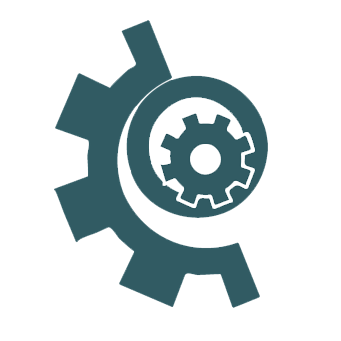

評論留言区